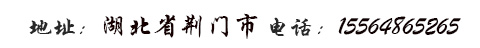喀耳刻书评满足现实中女性的乌托邦
|
北京白癜风医院 https://yyk.familydoctor.com.cn/2831/schedule/ 《喀耳刻》总体称得上是一部反映女性成长且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反正典神话小说,作者拒斥传统神话中菲勒斯中心的立场,赞美不甚符合传统男性审美、具有一定反抗意识和独立人格的女巫喀耳刻。但仔细看来,似乎并不应给予其如此斐然的评价。不难看出,《喀耳刻》中的除女主人公之外的主要女性角色形象比较单一、固定,看不到她们的立场和诉求,是功能性的角色。她们拘囿于男性欲望下传统女性形象,或是因外貌出众博得众男神倾心追求的女神们,尽管美丽的外表下可能包藏着狠毒的内心,为了私欲可以极尽所能、罔顾一切;或是聪敏贤惠、贤良淑德,如守候奥德修斯归来的佩涅洛佩。 我认为小说的书写显出一种隐藏的厌女倾向,除了作为女主人公的喀耳刻,别的女性形象几乎都是被贬低的、较负面的。女主人公又是怎样的呢?出生时被母亲珀耳塞形容“像一坨腐肉”,赫拉女王评价“她的头发像猞猁毛一样,有杂色”,兄弟姐妹们笑话“她的眼睛像尿一样黄,她的声音像猫头鹰一样尖。” 一方面,通过外貌不佳受到嘲讽和排挤凸显喀耳刻被众人孤立的地位;另一方面,作者通过外貌的区分将喀耳刻以外的女性“他者化”,因此喀耳刻将自己当作众宁芙中的例外而拥有一种“外部”视线,从她的视角出发似乎可以轻易窥见光鲜之下的“丑恶”。在她认为斯库拉蔑视格劳科斯,却依旧选择与他在一起后,喀耳刻产生激愤、嫉妒的心理,她厌恶的不是格劳科斯朝三暮四、见异思迁,是斯库拉魅惑人心。喀耳刻轻而易举地就站在“厌女”的那一方,厌女的根源乃在于父权制。 喀耳刻与女性角色中的任何一位都未能缔结不依附于男性之上的、更加纯粹的关系,也就不足为奇。她们身为父权体制下的牺牲者,无可避免地爱慕男人而憎恶女人。无论是“异类”的喀耳刻,还是徒有其表的宁芙、被狂热爱慕的女神们都只是一个载体——父权制文化下女性符号的具象存在。她们的恶毒、善良、魅力、反抗之所以显得脸谱化,是由于作者只停留在行为、语言的表面,未着力挖掘其背后的结构性问题。 相应地,与“厌女”并列的“慕男”在文章中表现为男性形象刻板化,是典型的浪漫小说式笔法。格劳科斯是喀耳刻的初恋,未变为海神前脆弱、单纯、将喀耳刻奉为女神;赫尔墨斯身份尊贵、俊美浪荡、来去无踪,典型的“霸道总裁”形象;代达罗斯和她同为“囚徒”,因此惺惺相惜,成为知己与情人;奥德修斯睿智沉稳、有勇有谋,是希腊英雄的典型代表;戈勒玛科斯温柔沉稳、不贪恋权力金钱,愿意陪伴喀耳刻一起冒险。 作者在文本中无休无止地提供满足现实中女性的乌托邦愿景,女性的个体性和自我感知与接受男性的呵护照顾可以并存。或许是对女性力量的不信任,又或许是现实的一种幻想性补偿,但我认为作者不必也不该囿于如此浅薄的视角,在女性成长的小说中选择绕过父权制意识形态的矛盾以实现其表面上的消除。 喀耳刻的真正存在及生命成长在基于“厌女”语境下的阐释中被削弱,推动女主人公成长的种种情节最终宿命般地落入平庸、循规蹈矩的浪漫小说套路:开篇基调是女主人公的情感孤立和巨大的失落;结局是从孤立无援和几近毁灭的威胁中走出,实现与男性的链接,获得一个稳定、完整而成熟的身份。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nsiduna.com/jsddx/11360.html
- 上一篇文章: 古希腊艺术与神话透析古希腊神话与艺术
- 下一篇文章: 同心自相知,同声自相应苏丹各界同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