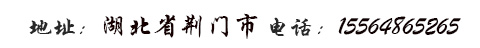给母校献上九百九十九朵枚瑰辛
|
灯光要注意以免使健康带来影响 http://www.zgbdf.net/baidianfengjiankangzixun/baidianfengpinglun/m/30732.html !给母校献上九百九十九朵枚瑰 忆昔师专上学时 ◎辛轩 年元旦,隔壁宿舍贴出新年对联:三年一瞬教室寝室图书馆;一日三餐清汤洋芋浆水面,试图对我们师专三年中的学习和生活进行总结。记得撰写此联时,同学们对上联内容大加肯定,认为较为准确地反映了我们班同学三年来的学习与生活实际,但是对于下联的内容,却有人并不认同。说师专的伙食可好了,当时我们每人每月31斤面票、23元菜票,吃得饱饱的。那时候灶上有馒头、油饼、炸酱面、土豆片等等,逢年过节还有饺子、面皮、红烧肉,比我们老家过年时都吃得好。尤其炸酱面,好吃得不得了,为此有人还将我们学校的校名戏称为“添水(天水)吃饭(师范)专喝(专科)学校”,怎么老是“清汤洋芋浆水面”呢?吃浆水面只是因为部分男生为了节约一定的菜票换烟抽。当时一包采宝牌香烟二毛钱,而吃浆水面只用五分钱菜票,吃三次浆水面就可以节约两包烟的菜票,而菜票又可以直接拿到校门市部去,用相等的面值换烟。然而在具体书写时,正是由爱抽烟的同学执了笔,才最终写成了这个样子。 我们班的同学大多来自艰苦的农村,吃过苦、受过罪,对学校的伙食非常满意。我入校第一顿吃饭,即给我留下了很深的记忆。那天开学,堂哥赶着骡子将我的行李驮到太京,送我搭上班车后来到学校,一进校门即碰上吃晚饭,大师傅接过我的碗,边舀饭边道:下次来时换只大点的碗,接着便给我打了高高一碗烩面片。 我的学上得不容易,能在师专上学是我多年所盼。我爱当老师,说心里话,我这辈子最大的理想,就是想当一名老师,平平淡淡,教书育人,但熟料阴错阳差,最终却干了别的。高一那年我辍学在家,只因在家劳动而饭量大增,我们全家的半锅稀粥我一人会吃去大半,父亲认为这样下去不成,他知道我上学时两只洋芋,一把熟面粉就是一天,说我上学不费饭,要让我继续上学,我便就又继续上了学。我们那时高中是两年制,我高二毕业参加高考预选,一预选就落了榜。父亲见我没有考上,便要让我回家种地。因为那时刚开始改革开放,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父亲说随便在荒坡上一镢头下去种几窝洋芋,秋后就会有饭吃,可是这时的我却不再这样想,因为我已经完全明白了跳出农门的好处,我不会像他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修理地球,我要考学,要考大学。我清楚我之所以没有考上,就是因为没有好好学习。我上小学时正是“文革”时期,我们多日子和社员一起劳动,念书很少,升初中时见零不取,即便这样也有五分之一的人没有考上。上初中时我经常陪和我一个村子的同学逃课,而我们每次逃课后,上课时老师便不让我们听课,而罚我们长跑、打扫厕所等。初中毕业后,和我一个村子的同学都不再念书,我也就跟着辍了学。我上高中时,学校一直没有英语老师,数学老师也因妻子有病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上一节停一节的,以致我们全班21人那年预选时只有一人通过了预选。我虽然连预选都没有通过,可是我却执意要去复读。因为这时,邻村或者邻乡不时传来有人考上了大学,山沟里飞出了金凤凰。不仅这样的事例一直鼓励着我,而且我给自己占过一卦,卦象说我也能考上。那天我正在锄玉米地,突然暴雨骤至,我便躲在山崖下,向天问卜道:请苍天明示,如我能考取天就速晴;否则就一直下到晚上,其结果是老天爷立马晴了。 我要去复读,可是家里掏不出学费,我便告别父母,开始了自己的筹措。我贩菜水、赶麦场、打短工,一分钱一分钱积攒。我在城郊帮人挖洋芋,挣上一元半角;我替人拉煤、卸车、赶骡马;我赶一百多里的山路从城里挂上蔬菜,背到牡丹的集市上卖掉,而我在西山坪村赶麦场时,一个天大的机会便向我走了来。那天午后天降暴雨,我全身淋透回到东家,主人将他儿子的衣服让我换上后,说:看你伶伶俐俐的,是能念书的娃,只要转到城里来,你就一定能考上大学,就这样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天水市四中的学生。四中时我清楚自己的短板是英语和数学,于是我就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这两门课的复习上。高考罢、夏收结束后我进城打探消息,原来我已成为四中当年上榜的学生之一。那时谢成老师四处联系不上我,急得无法可想,一见我,又气又喜,他让我速去中华西路招办院子参加面试,而我刚走了一圈正步就被打了下来,考官给出的理由是我腿跛着。我穿着一双新鞋,走了一百多里山路,脚上早打上了血泡,怎么会不跛呢?可是他说车费可以报销,你为什么要步行?就这样我又落榜了……再复读一年后,我终于考上了师专,您说,我能不感到幸运吗? 考上师专等于跳出了农门,相互一打听才知我的高考语文成绩很低,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便鼓足勇气试图转到数学系,班主任俞齐进老师鼓励我道:成绩低不可怕,怕的是能不能认真学,学习是一辈子的事,你才多大,怕什么!何况语文又关键在于平时的积累,只要你肯下功夫,广泛阅读,我相信你能学好。本来我一见俞老师就很崇拜:高大、儒雅、博学,早就听说了他的《金花与银花》等深受观众喜爱的戏剧作品,用同学们的话说,一看俞老师的儒雅劲就知道他准是大学教授,而这会儿您正这么和蔼地开导着我,我真是如浴春风,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学好中文。 原来学习中文太美了,能在中文系上学是我此生最大的幸福。关关睢鸠,在河之洲;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汉赋唐诗宋词,美仑美奂,浩瀚无垠。给我们教先秦文学的是王义、聂大受二位先生。王义先生身体瘦弱,每节课上咳嗽不止,可是他却拖着多病之躯,硬是没有耽搁一节课。只记得先生满腹经纶,从《诗经》的风雅颂,赋比兴开首,接着楚辞、左传、乐府,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把先秦文学的瑰丽与曼妙,那种古色古香的古典美,博大精深的知性美,讲解得头头是道,精彩之极,我们在下面也听得如醉如痴,心领神会。给我们讲授唐宋文学的是李继祖先生。李先生学识渊博,是《唐宋词鉴赏词典》的主要撰稿人之一、陇原大地有名的唐诗研究学者。记得先生讲“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中“才”字的用意时,用两个老太婆分说各自母鸡下蛋的事例道:我的鸡一天下一只蛋一天下一只蛋;另一个道:我的鸡一天天才下一只蛋。先生分析道,虽然两个老太婆都是叙说自己的母鸡每天生一只蛋的事实,可正是后者置入一副词“才”,便立马体现出她的母鸡生一只蛋的不容易。同理,诗人羁旅中的乡愁,也正是因这个“才”字而更显深广。又如“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向潇湘去”句。先生讲解道:无理有情,无理而妙。好像词人在对郴江说:郴江啊,你本来是围绕着郴山而流的,为什么却要老远地北流向潇湘而去呢?这难道不是词人反躬自问而慨叹身世:自己好端端一个读书人,本想出来为朝廷做一番事业,正如郴江原本是绕着郴山而转,谁会想到如今竟被卷入一场政治斗争漩涡中去!凡此等等,都被先生讲解得活灵活现,妙趣横生。及至后来我观看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栏目时,常常把那些大学问家和给我授过课的老师做比较,我觉得,诚如李继祖、王义等先生们中的任何一个,与他们相比,都毫不逊色。 给我们讲授“中国现代文学”的陈冠英先生常说:我教了好几届学生,你们班最好学了,凡我开出的书目,我在备课之前去图书馆,竟然全被你们班的同学借光了。陈老师学高为师,教书育人诲人不倦,至如今我还能想起他讲《薄奠》《春风沉醉的晚上》时的情景:舌生莲花,感情充沛,声情并茂。本来他担心现代文学作品阅读量大,我们看不过来,便亲自将一部分作品缩写成了精简版,可是我们班的同学,便是如《子夜》等读起来颇为费事的作品,也都是一个字一个地啃掉。给我们讲授当代文学的是青年才俊马超先生。马老师讲课和陈老师一样,口若悬河,妙语连珠,且声音充满磁性,特别好听。他从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郭沫若到“三红一闯”(《红日》《红岩》《红旗谱》《闯业史》),到“左联”作家,到“李(《红灯记》中李玉和)江(《龙江颂》中江水英)青(《红色娘子军》中洪常青)光(《智取威虎山》中郭建光)荣(《林海雪原》中杨子荣)伟(《奇袭白虎团》中严伟才)大(《白毛女》中大春)”的样板戏,娓娓道来,如数家珍,真如春风化雨,令我们陶醉。 啊!原来中国文学博大精深,美妙至极。原来汉字可以组合成“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悦目谁家院”“端来的酒和食,尝着是土和泥。倘若便是土和泥,也有些土气息,泥滋味”这么美妙的东西!而我,正是万分幸运地读到了。而且,还有着一位位先生们当头棒喝般的指点。我们体会着“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的真挚;享受着“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明快;感受着“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怅惘;欣赏着“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的诗情画意,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硬气,都在潜移默化地熏陶着我们,教化着我们,让我们渐渐明白: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也许因为我们班是中文系第一个三年制班级的缘故,学校对我们班格外重视,处处给我们开小灶、吃偏食:配备学校最攒劲的老师,提供最先进的教学设备。诸如图书馆、阅览室、电教馆,等等,都一路给我们班开绿灯。记得当时陈晓旭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刚出录像带,仅有的一个电教馆,便成了我们班同学观看的专利,真是让外语、数学等系的同学们羡慕。与此同时,班主任俞老师还跟天水市歌舞团取得联系,他们每出新的剧目,都要想法争取让我们观看。而我们每看罢一出,他又要及时组织我们进行讨论。从题材到表现手法,从主题到艺术特色,俞老师总是和我们坐在一起,鼓励我们互相争论,启发我们各表观点,而他又能精准地予以点拨,真让我们有醍醐灌顶之感。记得我们讨论荒诞剧、川剧《藩金莲》时,我想起了秦腔《双出五关》和《拾黄金》,因为《双》剧与《藩》剧一样,都是把时间上不同朝代的内容置于同一出剧中;《拾》剧与《藩》剧一样,都是把好几种表演形式混搭组合在一起,如秦腔、眉户、民歌等的混搭。俞老师面对我的疑问,更是因势利导,循循善诱,又为我们讲起了啥叫荒诞剧,以及荒诞剧的特征。正是由于他教法别致新颖,形式丰富多彩,文学理论中那些诸如悲剧、喜剧、典型、灵感、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颇为抽象的东西,也渐渐地为我们所领会;黑格尔所谓的“这个”而不是“那个”的确切含义,也渐渐地为我们所领会。同时顺理成章,他所教我们的“文学概论”课程,也在当年的统考中,平均成绩达到81分,获得了在全省五所师专中名列第一的好成绩。 给我们讲授“中国通史”的是张平辙先生。张先生学养深厚,他和张鸿勋、雒江生先生在当时的天水师专名气很大。先生一张口即公刘、古公亶父,或者一段楚辞,一首乐府的,说老实话,他老人家写的文章我到现在也看不很懂。张鸿勋先生虽然给我们讲授选修课“敦煌学专题”,但先生的课是显学,上课时我们只有尽其所能的认真听讲,尽其所能的记上笔记。先生也是只讲一些最基础的内容,稍微深一点的内容,我们根本谈不上听得懂与听得明白,更谈不上登堂入室。对先生及敦煌学的进一步了解是在十年后,我在教育学院进修本科时,当时给我们讲授“敦煌学专题”的何先生在课堂上曾提到先生,讲先生在敦煌学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与地位,看得出他对先生的学术成果很是推崇。当然,幸运的是,接下来,我有了向先生和雒江生先生当面求教的又一次机会。年,天水市政府开始编辑出版《天水历史文化丛书》,聘请张、雒二位先生统审稿,我是其中《文明曙光》《风物流韵》《人文撷英》三本书的编辑,在一年的时间内,多次坐在两位先生的身旁,聆听先生们对天水地域历史文化的讲解。同时又因我是他们的学生,两位先生便对我青眼有加,凡我的每一个疑问,都要不厌其烦的讲解,直到我弄明白为止,而我呢,自然明白机会难得,便抓住一切机会,试图能从先生们处多学一点。雒先生在《诗经》的研究上成果辉煌,我便有意拣“秦风”中的《无衣》《蒹葭》《渭阳》《晨风》等篇章,向先生虚心求教。 “三年一瞬,教室、寝室、图书馆。”虽然来去匆匆,三年时光转瞬而逝,可这三年时光却给我留下了终生永不磨灭的记忆,成为我人生中最为美好的时光之一。三年中,我学到了知识,增长了见识,结识了众多的师长、同学,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在你们的言传身教中,潜移默化,我的兴趣爱好渐次形成,我由一个怕中文专业转变到了爱中文专业;我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也渐次树立起来。你们,才是我人生中真正的贵人,正是有了你们的帮扶与影响,我接下来的生活与工作才充实而幸福。 我永远忘不了教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王喜明、教“外国文学”的王正威、教“法律常识”课的崔亚军,以及王元忠、王锁林等青年老师。当时,你们刚从名牌大学毕业,年龄跟我们差不多,可正是你们,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我也正是从你们的身上,学到了如何做学问,特别是如何做人。记得当时每逢张鸿勋、李继祖等先生的课上,你们竟也和我们班的同学坐到一起,也成为学生中的一员,认真听讲。你们这种谦虚好学、虚怀若谷的精神,永远成了我学习的榜样。而课后,你们又像兄长一样,关心我们的生活,让我们非常开心快乐。 我永远忘不了我们班的12名女同学,你们个个,心底善良、端庄美丽、气质高雅,尤其你们的勤奋好学,更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你们总是比我先到教室,比我迟回宿舍,你们的大多学科的成绩,都要让我努力追赶。以至后来,正是你们,成了我选择对象时的参照标准。我永远忘不了宿舍的另外7名舍友:见多识广、英年早逝的马孝刚、李秀俊,乐于助人、勤奋踏实的袁元、田继忠,舞姿优美、潇洒大气的张和平,才华横溢、诗名远播的王纪善,老诚持重、满头卷发的陈闯。永远忘不了我的同桌丁念保,是你,从陇西师范破格升入天水师专,又从天水师专破格升入西北师大,你和我每天比赛背颂的诗词,夯实了我的文学基础;比赛背颂的情景,成了我此生最美好的回忆之一。永远忘不了经常和我一起散步的苏定君、赵世荣、郭昭第、杨建增。定君兄英年早逝,让我疼肝疼肺。世荣老诚持重,一如兄长。昭第博闻强记,勤奋好学。建增忠厚老实,笔耕不辍。永远忘不了杨皓、张鸿儒、陈询、张小虎等人一手潇洒的钢笔字体;刘怀宇、李昭梅、刘小龙、刘惠芳、郑文燕、李红霞等人或一口流利的英语,或圆润的歌喉,或优美的舞姿。永远忘不了我们成立文学社团、创办文学刊物的情景:赵胤生刻写的蜡版、王荣的童话《过年》、郭昭第的小说《假面具》、张亦非的散文诗《青春狂想曲》,等等,或工整、或朴拙、或清新、或阳刚,以至于毕业前夕,我们全班46人中就有岳海明、桐欣、周克勤等10余人的作品,登上了《飞天》《星星》《诗神》等省内外专业文学刊物。而其中丁念保和马春仙的小说、苏全洲和王纪善的诗歌,都曾在当时的甘肃文坛引起了一定的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nsiduna.com/jsdgk/4869.html
- 上一篇文章: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招生专题现代信息与物流系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