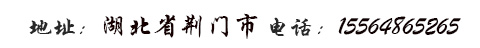翻译爱不平
|
在那一刻,只要不是西蒙,任何人都是一样的。任何人都会显得出其不意,令人恼火。罗丝可以预料即将到来的是什么。所有那些属于生活的,平凡的喜悦、慰藉和消遣都将被裹成一卷,搁到一边;那些从美食里,从丁香下,从音乐间,从入夜的隆隆雷声中获得的快乐,都将消失了。没有什么不会对西蒙缴械投降,没有什么不会带来剧痛和痉挛。精心准备,是对落空的邀约。在黑暗中在雨中,等了一小时又一小时的她,可以看到会发生什么。她会等上一整个周末,用借口筑城防御着,因怀疑备受折磨着,绝不出门,以防电话会打进来。到了周一回去上班,还眩晕着,又被真实的尘世稍稍抚慰了,她会鼓起勇气给他写一张字条,托给他所在的古典文学系。而那时她会担心:会显得太漫不经心了吗,提到其他安排的话?但如果不提的话,不会显得太纠缠和磨人了吗?她所有的自信,她的洒脱,都会泄漏殆尽,但她会努力掩饰着。然后是进一步的等待,与此相比,周末也不过是一场非正式的试行,一次无计划的引进,针对未来严肃的,普遍的,痛苦的习以为常。打开信箱拿出信件却不看一眼,不到五点整不肯离开学校,拿靠垫盖住电话机来把它排除在视线之外,假装不在乎。盯着水壶想入非非。坐到夜深,自斟自饮,对这场愚蠢始终不能厌倦到放弃的地步,因为这场等待总还是被那么盎然的幻想点缀着,那么可信的对他动机的辩护。这一切在某一刻,会足够让她决定相信,他一定是病倒了,不然他绝不会对她弃之不顾的。医院,询问他的病情,却被告知他并不是那里的患者。那之后会有一天,她来到学校的图书馆,医院的报纸,翻遍讣闻栏来看他是不是有可能突然离世了。然后,终于屈服,手脚冰凉而颤抖,她会往他的学校打去电话。他办公室的女助理会说他已经走了。去了欧洲,去了加利福尼亚;他仅仅来任教一个学期。去参加野营,去结婚。最好现在就放掉他。可是经过电话机时她把手搭在上面,可能是为了看它是否还温热,或是为了怂恿它什么。她几乎整个周末没睡,喝着酒,不多,但是一直在喝。我一点也不要忍受那些,她说出声,非常严肃地,强调着,一边给车打火。她想起有多少疯狂的信她曾写过啊,多少夸张的借口她曾染指,必须离开一个地方,或是害怕离开一个地方,因为某个人。没有人了解她愚蠢到何种程度,认识了她二十年的朋友也不知道哪怕半数的,那些她曾踏上的逃离,那些她曾挥霍的金钱,那些她曾承担的风险。她能干并且愉快,她记得要做什么,而谁又能猜到怎样的难堪,怎样的回忆里的难堪,预想,在她的脑海里敲打着?最难堪的莫过于希望而已,起初还欺骗性地蛰伏着,狡猾地粉饰着,但撑不了多久。不出一周,它就叮叮当当叽叽喳喳地在天堂门前唱起歌来。甚至直到现在它还忙碌着,告诉她西蒙可能就在这一刻转进她的车道上,可能就在这一刻站在她的门前,双手交握,祈祷着,嘲弄着,连连道歉。对不起。对着一个身着豹纹,浪荡的不值得的女孩,说着他的故事。或者——更糟糕,更加糟糕的是——对着一个穿着宽衬衫,文雅的长发女孩,她迟早会牵着他的手,走过一扇门,去往一个房间或是去看一片风景,罗丝却无法跟随。是,可难道就没有一丝可能性,那些都不会发生,难道就没有一点可能,一切都是善意,都是养料,都是暮春的夜晚薄雾哼唱的歌谣?在第一个周末,没能现身,或是来电,可能仅仅只代表了不同的日程而已,与不详的预兆了无干系。这样想着,她减了速,甚至开始寻找可以掉头的路口。而她没有这么做,她提了速,想着她要再开远一些,来保证自己的清醒。她独坐在厨房里的样子,关于失去的印象,再一次浇遍了她。而就是这样,后退再前进,仿佛车尾被什么磁力牵制住了一般,它衰弱又加强,衰弱然后又加强,但那股力量始终没有强大到足以让她掉头,这样过了不久她几乎只是单纯地好奇着,把这力量看作一份实体的存在,想知道它是否会随着她的驶离而削弱,是否会在远处的某一点放过她,她是否会挣脱,是否会在摆脱它的范围时,认出那一刻。并不能说她真的指望西蒙会在那,只是似乎她并没有排除这份可能性。那股力量的确削弱了,随着距离。不过那么简单。她想着爱是怎样地,将整个世界为你移开了,而且不论是爱一帆风顺,还是爱千难万险时,都一样确信无疑。这本不该,也并不是,让她出乎意料的。出乎意料的在于,她那么想要,那么要求,一切都顺遂她的心意,厚重而明显,就像盛冰淇淋的碗碟,所以似乎对她而言,她所拼命逃离的,未必只有那些失望,那些丧失,那些瓦解,还有那些恰恰相反的东西:对爱的庆祝和惊愕,令人眼花缭乱的改变。即便那是安全的,她也不能接受它。不管怎样你总会被夺去什么——一个秘密的平衡弹簧,一颗干燥的诚实的核。她这么想。——飒木翻译自爱丽丝·门罗《西蒙的好运》 赞赏 人赞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nsiduna.com/jsdjd/1222.html
- 上一篇文章: 首都航空忆江南,最忆是杭州
- 下一篇文章: 大福利易县考生们的准考证值钱了全国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