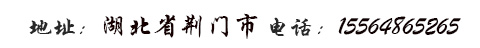谁能凭爱意将泰晤士私有
|
这条河,见证过亨利八世的盛大婚礼, 这条河,是透纳眼中伟大世界的缩影, 这条河,运输过黄金白银,煤炭布匹,养活了从造船工人到卖鱼小贩等无数行业的人们, 但无论是平民还是皇室,无人能凭爱意将这条河流私有。它属于伦敦。 泰晤士河,伦敦的脉搏,千百年来为这座城市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生机与想象。 千帆过尽,时光流转, 泰晤士河一直流淌,依潮汐起伏,或轻缓或汹涌,它那崇丽的歌声还未终结...... JosephMallordWilliamTurner– TheRiverThamesnearIsleworth:PuntandBargesintheForeground 泰晤士河一直是贸易之河。格雷夫森德种水芹菜的、图利街烤饼干的、搞托运的、沃平卖船具的、椴树舍搓绳索的,所有这些行业都靠泰晤士河为生。以河上贸易为主题的伟大绘画作品,都描绘仓库、精炼厂、啤酒厂、建材仓库,所有这些都印证这条河的权能和权威。它在城里的支配地位早在罗马人来临之前便已深入人心。早在公元前年,铜和锡就在这条河上运输,及至公元前年,由于河上贸易,构成伦敦的这片地方便开始支配埃塞克斯地区。也许正因为如此,宗教仪式的物件被掷进河里,从此一直沉埋着,及至新近考古才挖掘出来。 这座城市本身的特征和外观深受泰晤士河的影响。这座城市曾是“拥挤的码头和人潮汹涌的河岸”,河面不休地“划过勤快的船桨”。伦敦的动态和能量是马匹的动态和泰晤士河的能量。泰晤士河每日带进上千船队。威尼斯的桨帆船、低地国家的三桅船,争相抢夺河畔的位置。河面则挤满了驳船、渡船,载送市民过河。 17世纪伦敦地图 泰晤士河另一大贸易价值在于渔业,我们读到,15世纪有“比目鱼、拟鲤、雅罗鱼、狗鱼、丁鲷”,都是以芝士和板油为饵垂钓的。还有鳗鱼、大马哈鱼、鲤、七鳃鳗、大虾、胡瓜鱼、鲟。无数船只在河上做买卖。驳船、三桅船跟小舟并排行驶,还有双桨船,或者工人的划船、牡蛎船、渡船、蛾螺船。 大多伦敦人直接以河为生,或者靠河上运输的货物为生。14、15世纪的文献记载了众多泰晤士河职业,譬如,维护河道安全的“护河员”、负责涨潮时河堤或河畔建筑安全的“潮工”等。还有船工、捕鳗人、巡警、桨帆船工、渡船工、柴船工、水手、造船工、喊号工、打桩工、敲铃工、水警、水工。据记载,捕鱼的方法不下四十九种,诸如鱼网、鱼梁、围篱、柳条篮等。还有其他很多工种,譬如修筑河坝、堤防、漂浮码头、防波堤,以及修理水门、堤道、码头、河阶等。可以说,这是泰晤士河的早期阶段,作为这座城市发展和贸易的中心,一派生机盎然。 不过,这条河继而触动了诗人和编年史家的想象力。于是,泰晤士河成为一条壮丽的河流,王室和外交官视其为黄金大道。大游艇“张饰结彩,飘拂着丝绸彩旗”,其他航船“富丽地镶嵌着徽章标志”;很多船张起丝绸篷盖或帘幕,周围簇拥着划艇,满载着商贾或牧师或侍臣。正是在16世纪初这个时期,伦敦水工的船桨缠绕在河面的睡莲丛中,“伴随长笛的节奏”,那音乐令“木桨拍打的河水流淌得更快”。14、15世纪的水工们各自吆喝,泰晤士河总是跟歌谣和音乐密不可分。 17世纪,泰晤士河上的冰冻博览会(frostfair) 外交官进城或皇家婚典之时,可以听到更正式的音乐,这乐声不是随潮汐涨退,而是跟随历史的潮流。年,亨利八世及其第四任妻子克里维斯的安妮婚礼当日走水路前往威斯敏斯特,护拥他们的游艇“华丽地飘着旗帜、燕尾旗、彩饰”,游艇上“乐器演奏悦耳的旋律”。在亨利八世前次的婚典上,年,他的第二任妻子安妮·博林从格林尼治进伦敦城,“小号、桑姆管等各种乐器,一路演奏宏伟的旋律”。她的进城典礼是史册所载泰晤士河面最壮观的盛会,市长大人的座船领航,“艇上旗帜、燕尾旗飘摇,悬挂富丽的帘幕,游艇船身装饰金属盾形徽章,悬挂在金银丝带之下”。紧跟其后的是一艘平展的船只,颇似水上舞台,“一头怒龙腾跃,龙尾蟠屈,喷吐烈焰”。在这里,泰晤士河的自由激发了奢华的场面和音乐的灵感。市长大人的座船之后,追随着五十艘行业和公会的游艇,“全都装饰彩带,华丽非凡,船上载各种乐队”。贸易在泰晤士河面奏乐欢庆,而这条河本身就是财富的渠道。 年泰晤士河上的船只巡游,庆祝伊丽莎白二世成为英国在位最久的君主 然而,泰晤士河显然既能容纳较传统的货物,也能容纳超自然的力量。这条河流一向被形容为银色,是炼金术所用的神奇媒介,是斯宾塞的“泰晤士河银川”,继而是赫里克的“泰晤士河银足”以及蒲柏的“银色泰晤士”。赫里克还引入山泽仙女和水中精灵,但他的基调是传达一种忧伤的遗憾,被迫告别这条河,离开伦敦去乡间———不再有沐浴河中的夏日甜蜜傍晚,不再能去奇蒙、金斯敦、安普敦院游赏,不再能在这里“上船、下船,或者安全地抵达彼岸”。迈克尔·德雷顿也呼唤“银色泰晤士”,使用“最清澈的水晶之流”这个熟悉的比喻,蒲柏则形容它为“泰晤士老父”,“闪烁的银角弥漫着金光”。人们通常认为河川为伦敦城的雄性氛围增添女性气质,而泰晤士河却断无柔媚气质。它是“老父”,也许还有些可怕,或者原始,类似威廉·布莱克的“诺伯达蒂”。 从远处眺望,它似一片船桅森林;河面每日约有两千艘船只往来,还有近三千名水工,他们当时赋有十分恶劣的名声,横行霸道地把船摇向四面八方,载运货物。“伦敦塘”,也是伦敦桥和伦敦塔之间的这片地区,密密压压地、不留间隙地挤满了游艇、木桨船、大帆船,16世纪中叶一幅地图显示,船只泊在河阶旁,这些都是前往首府的中转站。在这幅地图上,街道几乎不见任何活动迹象,而河面则一片繁荣景象。这个夸张的手法诚然情有可原,因为其意图是强调泰晤士河的首要地位。在这里,有个伦敦故事很贴切。有一位国王,由于伦敦市政府不肯资助他的冒险活动,盛怒异常,便威胁说要将朝堂搬到温切斯特或牛津,市长大人答道:“陛下您尽管从容搬迁,您的朝堂、议会,尽管搬到您圣意所向的无论哪个地方,反正伦敦的商人仍有一大慰藉———您带不走泰晤士。” ?以上选摘自《伦敦传》,“你带不走泰晤士” ?本期编辑:Aisha ISBN:7 作者:[英国]彼得·阿克罗伊德 译者:翁海贞等 定价:元 点击阅读原文,现在就入手《伦敦传》!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nsiduna.com/jsdsb/5730.html
- 上一篇文章: 昆州8旬华人老妇家中身亡,丈夫被控谋杀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