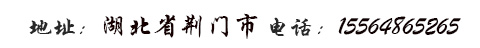女数学家之旅
|
作者:萧美琪毕业于台大数学系,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博士,现为圣母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为多复变分析与复几何。译者:林奕君毕业于台湾大学数学系。 中译文刊登于《数理人文》(订阅号:math_hmat)第7期(年1月),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父母亲——萧强、刘兰芳 眷村的童年年,我出生于台北市。因为国民政府在内战中败给共产党,我的父母和万大陆人在年一起迁徙到台湾,父亲当时隶属于撤退的国民政府空军。我出生时,上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两年后又添了一个弟弟。我的名字取自父母最喜爱的上海戏院(美琪大戏院依然还在)。他们很怀念--年对日抗战后,与我两位哥哥同住在上海的那段时光。他们总爱打趣说,女孩子在中国家庭没有地位,所以没多花心思在女孩的名字上。我的姐姐叫美琛,「琛」是一种玉,「琪」是另一种。男孩则依照家族传统属于「宇」字辈。 图1.父母亲和兄长德宇、振宇、存宇,姐姐美琛和弟弟昌宇。合影于台北植物园。年代的台湾是个很特别的地方。--年,这个岛屿曾受到日本统治50年,光复没多久的四年后,又有万人跟随国民政府从大陆四面八方流亡到台湾,加入原来的万台湾人口。我们在靠近空军总部的眷村长大,与外界十分疏离,当时像这样的眷村很多,眷村主要用来容纳几十万撤退来台的军人与眷属。我们住的眷村叫做「正义新村」,虽然称为村,其实很靠近市中心。其他眷村的名字像是:「忠贞」、「光复」、「建华」等,都强化了政府的政策。我小时候,来自共产党的威胁随时一触即发,我们成天受到政府宣传的轰炸,要为共军的入侵整备,更要准备在明年(永远的明年)反攻大陆、光复河山。正义新村里的居民都是空军家庭,来自中国各地,说着各式各样的方言。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故事,诉说他们如何在改变命运的年播迁来台的经历。父亲告诉我们他如何安排,让母亲和大哥、二哥坐上最后一班离开湖南的飞机。衡阳机场靠近母亲的故乡耒阳,而当时共军已经迫近。我母亲的故事说的则是她那天非常悲伤,百般不愿离开自己的老家,舅舅、其他亲戚及家仆伴着她到机场和父亲相会,一同飞往台湾。她万万没有想到,此去要再隔38年才能重返家乡。眷村的房子是在国军撤退的艰困环境中匆忙盖好的军房。以当时父亲微薄的薪水,养育六个孩子非常辛苦,另外他们还要适应在台湾充满不确定的新生活。但是对于在眷村长大的孩子,这里却像永不结束的夏令营。童年时与手足或邻居小孩尽情玩耍的时光,充满我最美好的回忆。每当父母亲出门留下六个小孩看家,我们就开始捉迷藏,把家里弄得天翻地覆。当时的我,完全不知孤独为何物。我最甜美的回忆之一,是秋天时与全村小孩一同在稻田里放风筝。虽然我们的眷村位于台北市中心,紧邻空军总部,但是当时另一头还有很多稻田。秋收之后,农人并不介意人们在田中的狭窄阡陌上行走。由于没有多余的钱能够浪费在风筝上,我们运用任何拿得到手的材料做风筝,先用细竹枝做骨架,再将旧报纸贴在骨架上。我们比赛看谁的风筝最美,谁的风筝飞得最远。一旦风筝线断了,所有人就会追着风筝跑,希望能收回值钱的线。当时,如果没把风筝线带回给母亲,肯定会挨上一顿好骂。那个年代物力维艰,资源宝贵,就算是一捆线也一样。农历春节过年也是令我印象深刻的回忆,眷村内过年是欢天喜地庆祝整整15天。丰盛的年夜饭后,鞭炮的声音响彻夜空,我们六个孩子整晚熬夜玩扑克牌,赌注是刚拿到手的宝贵压岁钱。新年假期的最后一天是阴历元月的第15天,也就是元宵节,习俗称为春灯节。这一天,眷村所有孩子都自己手工做灯笼。我的大哥德宇手很巧,总能做出最精致的灯笼。元宵节的传统食物是包着芝麻馅的元宵(类似甜汤圆)。吃完晚餐和元宵,家家的父母就把灯熄了,在漆黑的夜里,孩子们提着自己的灯笼,点亮蜡烛,开始在村中游行。全部总共不下百多个孩子,排成一条长龙,最年长的孩子走前面,到了队伍尾端的小孩,年纪约莫只有两岁。所有孩子都一同唱着:「灯笼来了!灯笼来了!咚,咚,咚!」反覆唱到午夜。没有人舍得回家,直到父母开始喊人才散去,不然就要受罚。我总记得那一夜回家后的心情有多舍不得,因为下个新年还要再等天啊!这些往事回想起来竟已如此辽远。此后20年,台湾从农业社会转型成为亚洲四小龙(其他三个是香港、新加坡、南韩)。我们眷村附近的稻田如今变成台北市最贵的地段,村子本身也已改建成大厦,眷村就这样走入历史。到我五岁时,同龄的小孩大多去上附近的幼稚园,但我不想去。比起坐在教室内,我毋宁更喜欢留在户外玩耍。我的父母没有逼我,但是在上小学前一年这段时间,他们也没先教我读书写字。我的父母不像大部分其他家长,不认为必须提早教育让孩子取得领先,他们相信这个阶段的小孩应该尽情的玩。虽然他们管教孩子相当严格,却也会让我们做自己喜欢的事。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位算命先生,母亲带我到邻居家给这位先生算命。这位邻居非常迷信,大力推崇这位算命先生。看到母亲带着一个早熟的五岁女儿,算命先生马上信心十足的说母亲没有儿子。经过邻居纠正,他才改口说母亲原本命中注定没有儿子,只因她上辈子做了许多善事,这辈子才有福气生儿子。算命先生成功化解了自己的窘境,继续赞美我母亲,说她长得如此福相,虽然先前多历苦难,好运即将降临。这种说词无疑适用并能取悦眷村里头的多数家长。最后,母亲顺带请他替我算个命。算命先生告诉她的,或许也只是一贯的陈腐套词:妳女儿长大后,将会聪明强健,胜过男子。母亲欣喜至极!几乎每天都在我耳边重复这句话,直到我离家读研究所。她总是说这位算命先生算得多准,而我也得一直提醒她,同一位算命先生还说她命中没有儿子。 台湾的求学历程 空军子弟小学我就读位于空军总部旁的空军子弟小学,校内有个大门可以直通空军总部,上头挂着一方匾额写着「空军子弟小学」,底下有行字注明「创于杭州笕桥」。中国空军在战前成立于杭州笕桥,因为地处偏远,在年特别为空军子弟的教育设立了小学,而后曾迁徙多次,抗日战争时搬至四川成都,后来又移至南京,年再迁到台北。就像当时台湾的许多事物一样,这个学校是原本杭州笕桥小学的难民版,只不过校长还是同一位。那时台湾大约有一打的空军附属小学,所有空军人员的子弟不分阶级都能免费就学,我的同学里将军与伙夫之子共冶一堂,学校是男女合校,而且没有制服,因为不是每个学生都买得起。虽然当时的官方语言是国语,而且学校禁止讲方言,但所有学生不分省籍依然不约而同的用四川话沟通。在家里,虽然只有大哥出生在成都,但小孩彼此也说四川话,父母亲则是用口音很重的国语跟我们说话。来自大陆各地的父母在台湾所生的小孩,就读位于台北市中心的小学,居然不断讲着四川话,这真是一个颇堪玩味的现象。长大后,无论是台湾人或大陆人,我都很难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我的母语是四川话。往好处想,这是一群来自不同背景却处境孤立的(难民)学生所蔓生的傲气,藉由宛如切口暗语的语言所提供的强烈认同感,发展出相濡以沫的团结情感;缺点却是让很多学生日后无法适应外面的世界。就在我年小学毕业后一年,台湾国民义务教育从六年延长到九年,台湾经济也在年代开始起飞,空军子弟小学后来全部变成公立小学。尽管如此,我日后还是经常遇见会说四川话的台湾人,如果他们与我年纪相仿,我通常都能准确猜出他们就读的小学。上小学的第一天,老师问起我的名字并要我写下来,我告诉她我不会写。班上大部分的小孩都上过幼稚园,已经会写自己的名字。而「萧」这个姓氏总共有19划,算是最难写的中文字之一。我记得听到我的老师跟另一个老师说起:「这是萧强的女儿,但是她竟然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家父是《中国的空军》月刊的总编辑,在军中略有文名。那天回家之后,父亲在纸上写下我的名字,要我记下来,这些就是已经六岁的我第一次学写的字。接下来几年,我每天在学校学几个国字,到了四年级突然领悟到原来自己已经可以阅读书报。第一件令我开心的,是我发现自己能读懂《西游记》,这本书是唐僧在孙悟空、猪八戒和沙悟淨的保护下赴西天取经的奇幻小说,这是我从小到大最喜欢的故事,也是我认真学中文的原动力。另外我还读过其他古典历史小说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通常这些书被认为是属于男孩子的故事,但因为家里有四个兄弟,我早已听过这些故事很多遍,不过能自己读还是感到热血沸腾。我的母亲抗战期间曾在武汉大学中文系就读,父母常常吟咏唐诗,让我也发现唐诗的美好天地。父亲非常高兴我对中国文学有兴趣,每个周末都会教我一些经典文章,他总希望我能成为作家之流,但我并不怎么当真。事实上,我对福尔摩斯和亚森罗苹更有兴趣,我小学最好的朋友玉潭也是他们冒险故事的同好,我们常常交换新到手的小说或漫画。我对小学算术很拿手,高年级时我们学到一些传统中国算术四则问题,这些问题本该能运用于现实生活。其中有种题型如下:鸡兔同笼:给定头的总数(例如头有8个)和脚的总数(例如脚有22只),请算出分别有几只鸡和几只兔子。我解这类问题完全没有困难,麻烦的是想不出要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应用。这些问题对于数学不好的同学很艰深,算错了还会被罚!对于那些读书跟不上还因为解不出这类问题而被体罚的同学,我总是寄以无限同情。上初中之后,我领悟到原来只要应用妥适的代数符号,就能够简单解出这类二元一次线性方程组的问题。小学的最后一年,大家都焦头烂额的准备初中职联招,我们是最后一届12岁就必须承受恐怖升学压力的小学生,一旦落榜,就不能再上学,也断送了未来谋求美职的希望。老师和家长一起威胁大家,如果不能通过考试进入公立学校,就只能送进放牛班。日后的高中联考和大学联招,我都不曾感受到如此沉重的升学压力。女子中学——初中与高中很开心的我通过考试,顺利进入我的第一志愿——台北市立女中(今金华国中)。一年之后的年,台湾国民义务教育延长到九年,初中职联招废除。那一年,台湾的12岁孩童平均身高整整高了两公分。延续日本中学男女分校的传统,我就读的初中全部都是女生,但依照国民政府的规定,无论是课纲的内容或公立高中数目,不分男女都必须一样。对女生而言,这尤其是一个很好的制度,我们和男孩分开受教育,但受教机会却是平等的。考试制度很公平,所有学生都是通过同样的考试进入公立学校就读,无一例外,所以班上学生来自台北各地的小学。这是我首度接触台湾本地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并非来自大陆。我觉得他们讲话的口音很特别,但我的四川腔偶而也会成为笑柄。我们在初中开始学英语,虽然我父母都懂英语,但他们从没教过我。我初次接触新语言的经验,大大打开了我的眼界。我无法相信只用26个字母就能表达一个语言中的所有字词。我们整个小学教育似乎都在学如何写国字,如果有人能为中文发明字母,我阅读中国古典小说的时间绝对远早于十岁!我像孩子学习语言似的充满热忱学习英语。父亲替我们买了林格风(TheLinguaphone)的英语教学录音带,这是一群语言学家所设计的英语教材,总共有50课,我大约花了一年时间把它们全部背下来,自然而然我的英语能力比其他学生好很多。我同时也非常迷摇滚乐,从猫王、披头四到金士顿三重唱,全都是很好的英语教材。我对英语的热情并没有持续很久。一年级之后的英语课都在学文法,每天都在练习记住如potato或bamboo复数型之类的东西,而不学习如何赏析英文文学或是其他有趣的内容。同时,我发现了另一门有趣的科目——历史。当时三年的初中历史课都教中国史,我们的历史老师一直是施曼华女士,她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老师。我总是迫不及待的想上她的历史课,因为觉得自己是要去听故事,而不只是上课。数学方面我依然表现杰出,也很享受上课的过程。初中的数学课包括代数,主要是解线性方程组和因式分解。初三要学欧氏几何,我非常喜欢基于几个公设就能写出证明的简单逻辑,这是我第一次对数学感到着迷。年我一如预期进入台北第一女中,这个学校创立于日治时期的年,当时的课程着重传统女性教育的题材,像是音乐、美术、烹饪和缝纫等。因为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女孩成为贤慧的新娘,于是成为知名的「新娘学校」。国民政府接管后,课程变得和男中一样扎实。在我就学的前两年,校长是传奇人物江学珠女士,她将一生奉献给学校,将一所新娘学校成功转型为学业表现杰出的名校。学校不仅要求我们的学业表现优良,也要我们擅长烹饪、音乐、美术和体育,而且至少在前两年必须参与学校的活动,三年级的学生则只专注于一件事,也就是通过大学联考,进入好大学。后来我才知道,很多美国女生从没有在高中参与团体运动的经验,这和我们的高中完全不同。当时我们每一班都要参加所有的运动项目,像是田径、排球、篮球和合唱比赛,甚至连每日课后的打扫都要列入竞赛。因为大家花很多时间在一起,我在高中结交了许多很好的朋友。高一时我对生物很感兴趣,尤其是读到遗传学的时候。高一结束时,所有学生都要在理科与文科中作出选择,我很确定自己想读生物。高二刚开始,国文老师就出了一个作文题目「我如何选择读理组」,由于我对自己的选择很笃定,因此就写了自己未来钻研生物学的种种规划,也许因为内容明确,这篇文章被选为范本,贴在布告栏供大家阅览。过了一年后,所有理组学生又得决定是要读丙组(生命科学含医学),还是甲组(物理与工程科学)。结果我却选择了甲组,放弃丙组。很多同学成天问我为什么改变心意,毕竟我在作文里写得头头是道。原因是我虽然喜欢遗传学,却很不喜欢解剖青蛙的经验,事实上我讨厌所有的实验课。高中的数学课本是一些大学教授根据新数学的观念撰写的,对很多学生非常抽象而艰涩,记得有一个学期的课本竟然直接从实数完备性开始讲起!高中的最后一年,我们班的数学老师是杨宽满先生,那学期的课程内容是组合学和机率,我表现非常好,连续得了好几个满分。杨老师总是在全班同学面前夸奖我,同时不断鼓励我读数学,那是我心中第一次这个想法具体成形。在联考选填志愿时,我就将台大数学系排在第一志愿,当时我完全没学过微积分。 台湾大学脱离课业繁重的高中生活,我和很多台湾学生一样,想要暂时喘口气,在大学里体验其他不同的生活面向。大一这一年,对所有学生都是新鲜的社交体验,因为几乎大家读的都是女校或男校,如今第一次回到暌违六年的男女同校生活。台大数学系那一届有45位学生,其中有九个女生。大多数男生都理着小平头,因为他们刚刚结束入学前为期两个月的军事训练。相反的,所有女生则是一头卷发,因为我们首次脱离发禁,可以自由留长发和烫头发。由于我是以最高分录取台大数学系,所以自然成为班代表。我很认真看待这项工作,常常忙于班级事务如班游、舞会等等,几乎没有时间读书。台湾大学成立于日治时期,当时称为「台北帝国大学」,校园里有很多西式建筑和成排的大王椰子错落成行。年国民政府迁台后,台大校长由前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先生担任。在他骤逝之后,钱思亮先生继任校长,成功的拓展学校,将台大转型为亚洲数一数二的大学。所有学生都是通过大学联招入学,没有例外,学费也几乎全免,对很多学生包括我自己来说,这是美梦成真。大家对自己新获得的自由与地位感到兴奋不已。大三以前的大学课程都很固定,没有太多弹性。我们大一要修微积分、线性代数和物理。我们的微积分老师是黄武雄教授,他是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劳森(BlaineLawson)的学生。线性代数则是一位受日本教育的老师教的,上课几乎都在讲矩阵运算。我这三门科目的表现只略高于平均,而且物理实验还差点被当掉。但是我的国文、英文、国父思想和中国通史,即使没怎么读书,成绩却都很高(大一每学期共有七门必修,再外加体育课)。很多同学常怀疑我以最高分录取并不是因为数学能力,而是因为英文和国文的高分。如今他们那种「你们女生不行」的想法似乎得到了验证。进入台大的第一学期过后,这类言论竟然在部分男生之间公开热烈流传,有些男生甚至罔顾女生的心情在我们面前直言议论。我从没遇过如此负面的学习环境。以前在女中,老师总是非常鼓励我们,让我们相信自己可以做到任何事!到了大二,我开始认真学习,部分原因是基于男生的嘲笑,另外也是因为自己厌倦玩乐和闲晃的生活。大二的必修科目是高等微积分、高等代数、应用解析。高微课本是阿波斯托尔(T.M.Apostol)的《数学分析》(MathematicalAnalysis),我们的老师是缪龙骥教授。他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教学秉持着德国人般一丝不苟的态度。他在一个半学期内教完整本书,一页不漏;剩下的半学期他采用史碧瓦克(M.Spivak)的《流形微积分》(CalculusonManifolds)。我还记得有一堂高微课中,缪先生在黑板上写出海涅/波瑞尔定理(Heine-Boreltheorem):每个紧致集的开覆盖都有有限多个子覆盖。就从这个定理开始,我领悟到什么是现代数学,虽然这和我高中想的完全不同,但对我来说也不像其他同学想的那么困难。当时数学系有很多学生,在第一年或第二年后就转系了。大二的高代,我们用的课本是霍夫曼(Hoffman)和坤哲(Kunze)一起合写的《线性代数》(LinearAlgebra),以及赫尔斯坦(I.N.Herstein)的《代数选题》(TopicsinAlgebra),老师是林一鹏教授。应用解析的老师是杨维哲教授。他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上课不用特定教科书,但我从这门课学到许多重要的主题,包括拉普拉斯方程、格林函数,以及广义函数(distribution)。他几乎当掉所有学生,只有六人幸存,我是六人当中的最高分。大二过后,同学们比较尊敬我了,甚至选我为数学学会的会长。除了数学课之外,所有理学院学生都要学习两年的第二外国语。数学系学生原则上要学德文,但也可改修法文或俄文。我们的德文老师是一位优雅的教授,他在哥廷根取得比较文学的博士学位,但他对于教导一群没有学习动机的学生毫无兴趣。虽然我的分数相当好,但一年下来并没有学到太多德文。大三那年我决定转到另外一班,跟一位德国神父学。他在台大很受欢迎但也很严格。我从他的课上学到更多,但是成绩也比原来低很多。我总觉得德文文法很吓人,因此学德文从来不像学英文那么热情。大三时我修了缪龙骥教授的复变,用的课本是阿尔弗斯(L.Ahlfors)第二版的《复分析》(ComplexAnalysis)。他只用了一学期多就教完这本书,第二学期则改用他自编的讲义介绍奈瓦林纳理论(Nevanlinnatheory)。这些实变与复变的(盗版)课本都成了我多年来书架上的珍藏,尽管书页已经散离。另外,大三那年我还修了代数、微分几何和概率。我们的代数课本是雅各布森(Jacobson)写的三册《抽象代数讲稿》(LecturesinAbstractAlgebra)中的第一册。我的代数成绩一向都很好,但相较之下我还是更喜欢分析。 图2.大三的我,年摄于台大。 我在大四修了三门数学课:实变、常微分方程、几何专题。我也修了经济学,但觉得非常无趣。绝大部分的男同学毕业后要服两年兵役,他们正忙着预官考试。而我决定到美国留学深造,所以正忙着准备GRE、托福,以及寄送申请资料。我申请了好几所学校的研究所,有些是数学系,有些是统计系。当时,我还不确定自己能否成为一个数学家。第一封录取通知来自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我至今还记得当天(年1月28日)心中那份雀跃欣喜,因为我获得全额奖学金。之后我申请的所有学校都给我录取通知,包括哈佛大学统计所。当时台大数学系的学生在国外有很好的名声,被好学校录取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能得到普林斯顿和哈佛的入学许可仍然令人欣喜。有些老师认为我应该去普林斯顿,但其他老师认为读统计比较容易有成。我询问母亲的意见,她并不知道我也申请了统计所,骂我说:「如果你想读数学,就好好读数学,念什么统计?」她的观念里,数学的地位比较高,统计则是给做买卖的商人读的。她总看不起生意人。我跟她坦承自己害怕无法成为好数学家,母亲说:算命先生说你聪明强健,胜过男子,而且你总是遇强则强,遇弱则弱。其实有时候一个人需要的就是母亲盲目的信心,于是我下定决心读数学。在我决定去普林斯顿的同一天,我拿出罗伊登(H.L.Royden)的实变课本正心研读。我跟自己说:「游戏开始了!」 成为数学家 普林斯顿(--) 我在年7月抵达普林斯顿,先在附近的姐姐家住了几天,然后搬进研究生学院(GraduateCollege)。研究生宿舍外型如同城堡,比研究所手册的封面照片还要美丽!宿舍紧邻高尔夫球场,还有一座称为克里夫兰塔(ClevelandTower)的高塔。我趁暑假选了一门开给外国学生的英语课,课堂的学生来自全球各地。我每天背着大学同学送行时赠我的书包,徘徊在美丽的哥德式建筑和高大的老树校园中,刚来时所受到的文化冲击很快就被优美的环境给舒缓了。暑假的两个月后,我的口语英文已经大有长进。9月学期开始,我很惊讶自己竟然是班上11人中唯一的女性,另外来自德国的访问学生也都是男性。不只如此,整个数学所除了我之外,只有一位从化学系转来的女学生,看来数学所在我入学前并没有收过多少女学生。系上也没有女教授,只有一位德国女性讲师。我到普林斯顿的第一年,除了一些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认识的访问学者之外,这些就是校园中所有的女数学家。 图3.普林斯顿大学数学所年入学的新研究生。从左至右,前排:作者、GregAnderson、BrianWhite、RobertColeman、DieterBassendowski、MarkHeiligman;后排:JohnSniverly、EricJablow、ThomasGoodwillie、RoderickBall、WolradVogell、DonBlasius、AllanGreenleaf。小时候,父亲很喜欢跟我说女科学家的故事,其中一位是吴健雄,她是知名的物理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的第一位女性讲师,后来成为哥伦比亚大学首位女物理学教授。另一位女科学家是郑彩莺,她从东海大学毕业后,年成为普林斯顿第一位取得(生物博士)学位的女性,五年之后普林斯顿大学部才开始招收女学生。我到普林斯顿的第二年,数学系聘任滕楚莲为第一位女性助理教授。楚莲和我都是从台大毕业,也是北市女中和北一女的校友,只不过她早了我六年,我们很快就培养出患难情谊并成为好友。30年后,另一位台大校友张圣容成为普林斯顿数学系的第一位女系主任。普林斯顿数学系很特别,系上并不开设任何基本研究所课程,从一开始就让所有研究生接触最前沿的课程,自始至终完全沉浸在数学研究之中,既没有必修科目,也不打成绩。博士生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在两年内通过资格考。那是长达三小时的口试,内容包含博士生自选的两个进阶科目,以及三个基础科目:实变、复变、代数。我知道自己想读分析,但对于该读哪个主题却毫无概念。于是我决定修遍该学期所有分析课程,授课老师分别是冈宁(RobertC.Gunning),孔恩(JosephJ.Kohn),和史坦(EliasM.Stein)。虽然台大的老师已经先警告过我这些高阶课程的难度,我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对这个全新的学习系统是多么准备不足。一周之后,我不再去上孔恩的课,因为我对课程内容毫无头绪。两个礼拜后,我的焦虑已经到了怀疑是否要继续上课的程度。史坦的课名是「另一类拟微分算子」(AnotherClassofPseudo-DifferentialOperators),听课的人超过20人。我当时只懂一点微分方程,主要是拉普拉斯方程(Laplaceequation),但从没听过拟微分算子,更别提「另一类」的拟微分算子。我鼓足勇气去见史坦,单刀直入的问他两个问题:(1)我是否该继续听他的课,因为内容完全超出我的能力。(2)我究竟该不该读数学?史坦跟我说,他本来就不期待我或任何一年级研究生能理解多少他的授课内容。他说:「你看看教室的听众。」里头有一半是教授,另一半是研究所的高年级生。他建议我继续听课,或许一、两年内就能更理解内容。至于第二个问题,他说既然我都已经在这儿了,就继续待着看看事情会怎么发展。他还建议我读他的两本著作,一本是他和魏斯(GuidoL.Weiss)合著的《欧氏空间傅立叶分析导论》(IntroductiontoFourierAnalysisonEuclideanSpaces),另一本是《奇异积分与函数的微分性质》(SingularIntegralsandDifferentiabilityPropertiesofFunctions)。这两本书(盗版)我都已从台湾带来,澈底研读这两本书后,我的心情慢慢安定下来。我还是继续上课,但不再烦恼自己到底理解多少。我决定选傅立叶分析和多复变作为资格考的两门主科。由于我正在上冈宁的课,自然就选用冈宁和罗西(HugoRossi)合著的《多复变解析函数》(AnalyticFunctionsofSeveralComplexVariables)来准备考试。同时我也在复习另外三门基础科目,幸好我大学所受到的分析及代数训练十分扎实。但在资格考之前,每个学生还要通过外语考试,学生必须能用德文、法文、俄文三者择二来阅读数学课本。这时大学上过的两年德文派上用场了,我没有碰到什么困难,就通过冈宁主考的德文考试。但是我实在没有时间学法文,其他研究生告诉我主考教授每次都要求学生翻译同一本书,也就是威伊(AndréWeil)的《凯勒流形导论》(Introductionàlétudedesvariétésk?hlériennes),所以我就把第一章的英文翻译整个背下来。结果我去接受穆尔(JohnMoore)考试时,他却给我另一本法文微积分课本,要我翻译前面几页,他或许认为这样对我比较容易。我开始从第一页的Nombres(也就是「数」)念起,虽然大致猜得出意思,但却译得断断续续而且可能有错。最后我直接承认自己准备的是威伊的书,于是他拿威伊的书给我,要我翻译第一章,我就这样通过了法文考试。第一学年快结束的5月时,我通过了资格考。虽然起初有些跌跌撞撞,总算撑过了普林斯顿的第一年。通过资格考后,我决定跟孔恩研究多复变,因为我一直很喜欢复分析。孔恩是第一个解决强拟凸域(stronglypseudoconvexdomains)上的d-bar诺曼边界问题(Neumannproblem)的人,他的解被称为孔恩解(Kohnssolution)。我用来备考的那本冈宁和罗西的多复变数书中,使用比较属于代数理路的层论(sheaftheory),这和使用偏微分方程的孔恩方法完全不同。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阅读弗兰(GeraldFolland)和孔恩合著的《科西/黎曼复形的诺曼问题》(TheNeumannProblemfortheCauchy-RiemannComplex)以及孔恩的原始论文。一年后这本书几乎要被我翻坏了,同时我也渐渐理解这项主题。进入研究所的第二年,我依旧坐在同一门课名的教室里,但是课程内容于我开始生出意义。才一年前,当时这一切还全然无从捉摸。孔恩在课堂教他刚完成的论文内容,用乘数理想(multiplierideals)研究诺曼边界问题的充分条件,这是一篇影响深远的论文。一学期过后,孔恩教授给我正式论文问题之前的暖身题,要我研究片段平滑强拟凸域上的诺曼边界问题。我记得很清楚他告诉我说,他期待我在三到六个月内解决这个暖身问题,并强调这个问题不足以当作论文题目,真正的题目将与乘数理想有关。当时,柯西/黎曼方程(Cauchy-Riemannequation)在片段平滑强拟凸域上的解,已经在几年前被蓝格(R.MichaelRange)和萧荫堂以积分核(integralkernel)方法解出。因此他认为在这种域上的诺曼边界问题,应该只是例行性的习题而已。他要求我报告蓝格/萧这篇运用核方法(kernelmethod)解出柯西/黎曼方程的论文。由于缺乏核方法的背景知识,这个挑战对我来说非常困难。我囫囵吞枣的读完论文,并在孔恩的研究所课堂上报告,但其实要在许多年后,我才完全了解多复变的核方法。那时,我也在研读霍尔曼德(LarsH?rmander)的《多复变分析导论》(AnIntroductiontoComplexAnalysisinSeveralComplexVariables)。孔恩的次椭圆估计(subellipticestimate)、霍尔曼德的L2方法,以及核方法是解决柯西/黎曼方程的三大法宝。我后来才领悟,也许一开始就让学生沉浸在高深数学中并不是件坏事。研究生若能及早接触最前沿的研究,能培养出更宽阔的视野并学会独立思考(当然只限于能在学术界生存的人)。那时的我觉得自己难以胜任,而且有相同感受的人并不只我一个。进入第三年的研究生生活,系上和高等研究院的活动增加了。费夫曼(CharlesFefferman)在休假多年后,第一次回来系上开课;我修了弗奈斯(JohnE.Fornaess)的课,学到不少多复变的反例;那年我还去高等研究院上课,包含尼伦柏格(LouisNirenberg)和丘成桐的非线性微分方程课程。那一年是研究院的微分几何专题年,由丘负责筹划。每周三早上八点,丘成桐开始讲非线性方程,并介绍他对卡拉比猜想的证明,演讲厅坐满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家,我至今犹记得当时临场的兴奋感。那一年我认识了很多数学家,包括陈省身。在普林斯顿的每一天,我的身边有许多聪明绝顶的人,不仅是多复变的学者,还有其他领域的专家。偶尔难免会觉得畏缩,但更多时间则是种激励。我在普林斯顿很早就学到一件事,那就是想成为好数学家必须非常非常努力,但努力只是必要条件,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充分条件是什么(如果真的有的话)。我研究暖身题快一年了,却几乎没有成果,因此感到非常沮丧。在非平滑区域的情况几乎事事和孔恩的预期相反。平滑区域的边界值问题不能推广到非平滑区域,唯一的例外是基本的L2理论,那是年霍尔曼德重要论文就已证明的结果。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问题都仰赖新方法的发明,所以当时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为时尚早,因为就连简单一点的非平滑域如利普席茨域(Lipschitzdomain)上的赫吉定理(Hodgetheory)也都尚未解决。我那时只解出带锥形奇点(conicalsingularities)利普席茨域上的赫吉定理的几个特例,这后来成为我博士论文的内容。一般利普席茨域上的赫吉定理一直要到三十年后才解决。1年由朵丽娜.密崔亚(DorinaMitrea)、马里奥斯.密崔亚(MariusMitrea)和泰勒(MichaelTaylor)发表在美国数学学会的研究丛书《纪事》(Memoir)中。几年后,朵丽娜、马里奥斯和我又给了另外一个证明。当年的我,对于连暖身题都无法解决感到非常难过。前往圣母大学的曲折年夏天,我取得普林斯顿的博士学位后,便前往普渡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当时普渡数学系主任是鲍恩迪(SalahBaouendi),我前一年已经在罗格斯大学由特列夫斯(F.Treves)筹划的会议上见过他。鲍恩迪是一个精力十分充沛的人,研究上也很活跃,身边总是有很多活动和人群。我刚到普渡时,只知道自己不想再继续研究带角域(domainswithcorners)的问题。我参加了一些讨论班,而且常常和鲍恩迪与他的学生张清辉讨论。张清辉也是台大毕业生,他和鲍恩迪与特列夫斯一同研究向量场的实解析下椭圆性(real-analytichypoellipticity)。几个月之内,我找到了与他们问题相关的研究题目,不过是属于平滑范畴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特殊情况从孔恩/罗西理论已知为真,因此也和我以前的研究有关。我只花了几个月就解决这个问题。我一写完论文,那年在普渡访问的霍尔曼德的学生梅林(AndersMelin)却告诉我,我的结果之前就已经用艾格洛夫/霍尔曼德(Egorov-H?rmander)定理证明出来了,只要把问题给微局部化(micro-localized)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打击让我很震惊。虽然如此,鲍恩迪还是建议我将论文投稿,因为我的新方法本身有它的价值,只要清楚说明结果已由微局部分析的方法得知即可。于是我还是投稿了,而且文章也在同年被接受。鲍恩迪在论文与计划申请的写作上给予我很多非常实用的建议。他还要我以自己的研究向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申请研究计划,虽然获得补助的机会并不大。他甚至给我一份他的研究计划作为范例。他建议我研读孔恩和霍尔曼德的经典论文,并模仿他们的写作方式。我还清楚记得他有点直率的意见:「每个句子都要有逗号或句号,不要自己发明英文写法。」后来我也常常复述这些实用的提醒给自己的学生和博士后。我和普渡的合约只有两年,博士后研究的第二年,我得开始找下一份工作。由于我只有两篇被接受的论文而且尚未发表(另一篇是本于我的博士论文所写的论文),我并没有收到任何其他数学系的消息。到了三月底,正当我开始准备我的「B计划」时,德州农工大学数学系主任莱西(E.Lacey)打电话,邀请我去面试一个预备终身职(tenure-track)的职位。当时我只认识那儿的博格斯(AlBoggess),他也是聘请我的主要推手。我在四月拿到工作,就没必要动用B计划了。那年夏天,我和丈夫张学嘉结婚,他和我一样是普林斯顿的研究生,同样出生于台湾,但他八岁就离开台湾,先后住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最后才到美国。他当时任教于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分隔两地的「双体问题」对我们来说可是个大难题。德州农工大学位于一片田野中,就像普渡一样,只是德州什么东西都大一号。校园内还有项特色,就是军校毕业生特别多,他们总是叫我「夫人」(Maam),我花了一段时间才适应德州腔。在学术研究上,我们举办很多激发研究的讨论班,参与者许多是拥有共同兴趣的年轻学者。在我抵达的一年后,系上也聘用了玻亚斯(HaroldBoas)。博格斯是波尔金(JohnPolking)的学生,也是复分析核方法研究的专家。他在讨论班中给了一系列积分核的演讲,是一位很棒的老师,我就是在那里学到柯西/黎曼方程的核方法,以及切向柯西/黎曼方程。我在研究生时期读得很辛苦的蓝格/萧的论文,现在重新用哈维/波尔金(Harvey-Polking)的方法重新诠释就简单多了。不久,我和博格斯找到一个可以合作的问题,合力完成了关于切向柯西/黎曼方程局部解的论文。这是我第一次和另一位数学家共同研究,我深刻体悟到拥有伙伴的重要性。我们不但各自提出新点子与不同的视角,更在意见交流的过程中激发出意想不到的新结果。我依然继续研究切向柯西/黎曼方程解的大域L2存在性与估计。这个研究我从普渡就开始进行,我不断思考这个问题,写了两篇相关主题的论文,但想证明最主要的定理还有一项大障碍待突破。有一天,当我教完有限数学(高中数学)课后,一个简单的灵感突然冒了出来:用微积分的变数变换。当我反复思考清楚后,我立刻写下论文〈切向柯西/黎曼复形的L2估计和存在性定理〉(L2estimatesandexistencetheoremsforthetangentialCauchy-Riemann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nsiduna.com/jsdyp/7035.html
- 上一篇文章: 太极拳,成功申遗42项非遗项目,你知道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