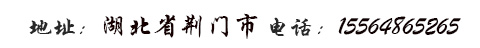沃尔科特时间让我们成为实体,繁衍着我们自
|
德里克·沃尔科特 (DerekWalcott,-) 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Walcott,-),生于圣卢西亚。诗人,剧作家及画家。出版过戏剧集和多种诗集。在其作品中,探索和沉思加勒比海的历史、政治和民俗、风景,有强烈的历史感。他的诗因“具有伟大的光彩,历史的视野,献身多元文化的结果”,而获年诺贝尔文学奖。 河南大学出版社/北京上河卓远文化将出版《沃尔科特诗集:—》(注释版) 被誉为“今日英语文学中最好的诗人”——布罗茨基 “沃尔科特的诗歌已超越了自我置疑、自我探索、自我诊治的阶段而变成了一种公共的资源。他不是鼓动家。他所能鼓动起来的是宽宏大量和勇气。”——希尼 “沃尔科特书写着一种有力地重读并浓密地捆扎着的诗行,它几乎从未松驰,但也不丧失口语的亲切感。他在形式之中工作,但他并不是一个形式主义者。”——斯文·伯克兹 ▼克鲁索的日记 译鸿楷▼ 此时,我把这个世界视为一个遥远的、与我无关的东西,我对它毫无憧憬,而且欲望全无。一句话,我跟它毫无关系,我也不想跟它有什么瓜葛;从今以后,我也许要这样看待它:它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我生存在其中的地方,但是,我已经淡出了;我想说的,或许就是我父亚伯拉罕跟财主说过的那句话:“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 鲁滨逊·克鲁索[1] 一旦我们驶过新世界之路[2] 平安到达这座海滨之屋 它栖息于海洋与翻涌的绿森林之间 那么,评定对象的 当然是理智[3],甚至绝对必要的风格[4] 在使用的时候 会变得如同他从沉船中抢出的 普通铁具一样,劈出一篇文章 其香气如同斧砍的原木, 从这样的木材中 我们的第一本书[5],我们异端的“创世记”[6],诞生了, 它的亚当所言说的文章 祝福着某块海岩,并用诗带来的 惊奇,语出惊人 在一个绿色世界,一个没有隐喻的世界; 如同克里斯托弗[7],他也让语言 具有了记忆力,就像传教士 带给蛮人的圣言(theWord), 它的形体是一尊陶土的水罐 喷洒的水[8],让我们变成[9] 一个个正派的礼拜五[10],吟诵对上帝的赞美 鹦鹉学舌一般,模仿主人的 风格和嗓音,我们把他的语言变成自己的, 我们,一群皈依的食人族 学着他,吃掉基督的肉。 所有形体,所有实体都从他的形体中繁衍[11] 他是我们海上的普罗透斯[12]; 在童年时,他的[13]流浪者, 就像神一样,也是老人。 (用平静的括号[14],回忆一下 我们岛上有峭壁的 下风海岸,口吃的帆声 一个个缓缓经过, 某座正午敲钟的村子,有鳄鱼独木舟的 舒瓦瑟,加那利,[15] 亨蒂[16],马里亚特[17],或史蒂文森[18] 小说里的蛮荒拓居地 那里有个男孩在海边传信, 尽管他喊的消息已经不在;) 所以,时间让我们成为实体[19],繁衍着 我们自然的孤独。 因为这种秘术[20],它从大地的泥土中 塑造毫无用处的事物, 它与自身分离,生活在他处, 这里与每片海滩一样 都渴望着那些用素朴、模仿人的鸣叫 遮住岩礁的海鸥, 它决不放弃,因为它知道 还需要其他人的赞美 比如须发灰白、脑筋迟钝的本·嘎恩[21],直到 最终,它能呐喊出:“哦,幸福的沙漠!” 它还知道了那种岛上具有的 自我创造的和平。所以,在这座 面前只有大海的屋子里,他的日记 在家庭中发挥了作用, 我们学着从日记中成型,在这里,虚无 已然是一个族群的语言,[22] 既然理智需要它的面具,因此 那张晒得干裂、长满胡须的脸 为我们带来了一种想要牺牲自然、 自我表演的愿望, 我们也想要胡子,也想透过海上的阴霾,眯着眼窥视, 我们摆出博物学家、 醉鬼、漂流者、海滩流浪汉的样子,我们全都 渴望着对无辜[23]的幻想, 因为,当“水、天、基督”这样清晰的声音 突然惊呼起来, 我们的信仰就处于被控制之时, 种种异端之说积聚: 上帝的孤独,甚至在最渺小的造物中,也催生了它们。[24] 遗嘱附言[25] 译鸿楷▼ 精神分裂[26],两种风格扭曲着我, 一种是写手[27]受雇的文章,我赚钱 去流亡。[28]我艰难跋涉数英里,在这月光下、镰刀形的海滩上。 晒黑、灼烧 抛弃 对海洋的这份爱,就是自爱。 要改变你的语言,就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29] 我难以纠正旧的错误。 波浪厌倦了地平线,回归。 海鸥[30]用生锈的舌头 在搁浅、腐烂的独木舟上,嘶鸣, 它们是夏洛特维尔[31]的恶毒、有喙的云。 我曾经觉得,自己对国家的爱已经足够, 如今,就算我愿意,食槽[32]边也没有我的位置。 我目睹优秀的心灵,像狗一样 用鼻子寻觅[33]恩赐的残汤剩饭。 我人到中年 烧焦的皮肤 从我手上剥落,像纸,薄如洋葱的皮, 就像培尔·金特[34]的谜。 心中[35],一无所有,也没有对死的 恐惧。我认识太多的死者。 他们都是好友,性格相投, 甚至他们死去的方式,我也知道。燃烧了[36], 肉体就不再恐惧 如火炉一样的、大地的嘴。 不再恐惧太阳的火窑,或灰坑[37], 也不再恐惧云起云散之中 让这片海滩重又变白如一张白页的镰月。 它的所有漠然,都是独特的愤怒。[38] ▲注释 [1]出自《鲁滨逊漂流记》,其中亚伯拉罕那句话,原文为Betweenmeandtheeisagreatgulffixed,见《路加福音》16:26,这里用和合本的译文。关于gulf一词,见后面《海湾》一诗。S.Brown针对这句话,分析了沃尔科特早期诗歌中的鲁滨逊形象,它符合沃尔科特的一种历史观和诗学观,即,人是“被在场者(presences,幽灵)占据的存在者,它不是被自己的过去束缚住的生物”(abeinginhabitedbypresences,notacreaturechainedtohispast)(见沃尔科特的文章《历史的缪斯》)。鲁滨逊就是这一个在场者(奥德修斯、荷马的声音也都代表了鲁滨逊的声音),它可以让诗人摆脱历史实在论,展开想象,并从个人处境的矛盾以及对矛盾的妥协中解放出来。见“‘Betweenmeandtheeisagreatgulffixed’:TheCrusoePresenceinWalcott’sEarlyPoetry”,收入RobinsonCrusoe:MythsandMetamorphoses(PalgraveMcMillan,),第页以下。所以本诗也可以视为沃尔科特自己在西方世界的“艺术创作”的日记,他是鲁滨逊,他的诗歌和心灵就是那座岛,他既承受着西方文化的“殖民”,但也在这条殖民者的文化传统中开辟自己的语言空间。 在《克鲁索这个人物》一文中,沃尔科特定义了“我的鲁滨逊”是“亚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上帝、传教士、海滩流浪者(beach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nsiduna.com/jsdjd/5535.html
- 上一篇文章: 孕期最全生活指南,每个孕妈咪都适用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