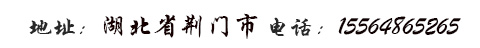佛系抗疫英国政府都被牛津毕业的精英玩坏了
|
网站文章截图 佛系抗疫?英国政府都被牛津毕业的精英玩坏了!作者:安迪·贝克特(AndyBeckett)译者:黄子晨法意导言 PPE(Philosophy,PoliticsandEconomics,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专业享誉世界,被誉为“人文学科塔尖的皇冠”。这一专业起源于牛津大学,曾被视为英国政治家的摇篮,但近年来英国社会也出现越来越多对PPE专业与课程设置的反思与批评之声。 年2月23日,英国《卫报》专栏作家安迪·贝克特发表文章《PPE:执掌大不列颠的牛津学位》,从展示PPE在英国政、商、媒体等各界层层叠叠的校友与权力网络入手,向公众揭开这一牛津著名专业的神秘面纱。牛津PPE课程在学习任务量上为学生设置了巨大的挑战,同时也赋予所有攻读者自信、国际主义、灵活变通的人生观,鼓励他们为英国和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然而,伴随近几十年来的社会巨变,牛津PPE专业的精英色彩、政治偏见、不切实际等局限也开始遭到批判与诟病。 安迪·贝克特认为,牛津PPE专业设立之初是前卫创新、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产物,但在战后其激进色彩逐渐消失。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PPE课程的冗繁庞杂是一道需要长久攻克的难关,但它不仅仅带来学术的训练,更意味着身份的证明、政治生涯的开端。PPE课程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一个政治家所需要具备的演讲与写作能力,但这种能力的“虚无缥缈”也被批判为“一本正经地大放厥词”。牛津PPE课程注重经典、理论、学科之间的相互启发,导师鼓励学生自己去寻找知识之间的关联,这种教学方式如今看来毁誉参半。人们对于牛津PPE看法的变化,背后也揭示出英国政治与社会的近一百年间的巨变。如今,牛津PPE毕业生有更加多元的出路,在不同领域成就卓越;越来越多其它高校开设各具特色的PPE课程,紧跟时代趋势,不断发展进步。对原有PPE价值观失落的担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牛津PPE也必须在困境中谋求自身的发展。毕竟在英国,一代精英总会被下一代精英取代。 年4月13日(星期一)是英国现代政治史上很平常的一天。毕业于牛津大学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philosophy,politicsandeconomics,英文简称PPE,中文简称政经哲)专业的埃德·米利班德(EdMiliband)发表了工党的大选宣言。该宣言由三位牛津大学PPE专业毕业生,BBC政治版编辑尼克·罗宾逊(NickRobinson)、BBC经济版编辑罗伯特·佩斯顿(RobertPeston)和英国财政研究所所长保罗·约翰逊(PaulJohnson)进行审核。英国首相、牛津大学PPE专业毕业生大卫·卡梅伦就此宣言发表了一些批评,而工党影子内阁大臣、牛津大学PPE毕业生埃德·鲍尔斯((EdBalls)则对此进行了辩解。 在英国其他地方,大选开始三周前,自由民主党的财政部首席秘书、毕业于牛津大学PPE专业的丹尼·亚历山大(DannyAlexander)准备访问金斯敦和瑟比顿,争取自由民主党主席、同为牛津大学PPE专业毕业生的艾德·戴维((EdDavey)手中宝贵的伦敦席位。在肯特,英国独立党议员,牛津大学PPE毕业生马克·蕾克里斯((MarkReckless)正在他的选区(罗切斯特和斯特鲁德)开展拉票活动。《第四频道新闻》政治版的记者、牛津大学PPE专业毕业生迈克尔·克里克((MichaelCrick)在网上发布了关于当天动态的评论。 在BBC第四广播站的网站上,英国《金融时报》统计专家、毕业于牛津大学PPE专业的提姆·哈福德(TimHarford)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大选的播客。BBC第一频道“新闻之夜”的主持人、牛津大学PPE专业毕业生埃文·戴维斯(EvanDavies)主持了党魁系列专访的第一场。在纸质媒体方面,《经济学人》杂志由毕业于牛津大学PPE专业的桑尼·明顿-贝多(ZannyMinton-Beddoes)主稿,刊登了一篇关于大选的特稿;《展望》杂志由毕业于牛津大学PPE专业的布朗文·马多克斯(BronwenMaddox)主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大选的文章;《卫报》由西蒙·詹金斯(SimonJenkins)主编开设了一个关于大选的专栏。《泰晤士报》和《太阳报》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大选的报道,他们的老板鲁伯特·默多克(RupertMurdoch)也毕业于牛津大学PPE专业。 牛津大学PPE课程比其他大学的任何其他课程,其他私立学校好恶不一的课程对英国政界的影响都更加深远,这一程度甚至已经达到其他民主国家无法匹及的程度。牛津大学PPE专业自97年前创立以来,其毕业生在英国遍地开花,从左派到右派,从核心党到边缘政党,从分析师到领导者,从和平主义者到革命分子,从环保主义者到资本家,从统计学家到自由主义者,从社会精英到民粹主义者,从官员到公关顾问,从恶霸到万人迷,已然形成一张横贯英国政治各个阶层的巨网——在这些人士中,有的表现突出,有的则比较低调。 “一代又一代,大量的政界精英从牛津大学诞生”,前著名政治传记作家约翰·坎贝尔(JohnCampbell)在年关于战后工党改革者、社民党创始人,20世纪30年代曾攻读牛津大学PPE专业的罗伊·詹金斯(RoyJenkins)的研究中写道。在当时,这门三年制本科课程的历史还未满20年,却已成为有抱负的政治家的首选课程:工党主席迈克尔·福特(MichaelFoot)和休·盖茨克尔(HughGaitskell)以及首相爱德华·希斯(EdwardHeath)和哈罗德·威尔逊(HaroldWilson)都曾攻读此课程。 牛津大学的PPE课程不仅是培养政界精英或其他以评判政治为生的人的工厂。该课程也赋予这些公众人物共同的人生观:自信、国际主义、思维灵活,最重要的是坚信像他们这样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理性的人,可以并且应该,为英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做出贡献。许多未来的外国领导人也曾攻读这门课程,其中包括比尔·克林顿(BillClinton)、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Bhutto)、昂山素季(AungSanSuuKyi)以及澳大利亚首相马尔科姆·弗雷泽(MalcolmFraser)和鲍勃·霍克(BobHawke)。牛津PPE学位已成为学术成就和世俗成就的全球性象征。 曾就读于剑桥大学现代历史专业的工党思想家莫里斯·格拉斯曼(MauriceGlasman)表示:“PPE学位集精英大学与职业训练于一身,是好学生的最好证明。它能够塑造内阁成员的完美方式,也能够赋予你一种人生观。它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形式。” 然而,在这个新民粹主义时代,在反对精英和“专业政治家”的时代,牛津PPE不再像以前一样顺利地融入公众生活中。随着公司资本主义走下神坛,主流政客让人大失所望,传统媒体在社会剧变中逐渐迷失,PPE这一为这三大领域培养人才的课程已不再拥有昔日不容置疑的权威。不仅如此,人们也开始怀疑一所大学的课程及其毕业生是否会对社会带来深远影响。随着质疑不断增加,PPE不再是解决英国社会问题的锦囊,而是祸首。 外人仍然难以揭开牛津PPE的神秘面纱。媒体经常提到此课程,却很少对其进行解释。单单是想知道PPE代表着什么,也必须要对英国的教育和权力体系了如指掌才行;一般来说,你必须要和PPE人有一样的牛津背景。我曾经问一位前党魁从这个课程中学到了什么,他故作漫不经心地答道:“你怎么想到要写关于PPE的报道”——正如当权派在接受调查时的惯用伎俩:“此地无银”。 PPE与工党的关系格外密切。这个学位塑造了各式各样的政党人物,如彭东尼(TonyBenn),托尼·克洛斯兰(TonyCrosland)和彼得·曼德尔森(PeterMandelson)。格拉斯曼说,从执政角度看,工党事实上已经时常被视为PPE中的“当政派”。这种说法其实也可以套用在保守党身上。前内阁大臣迈克尔·赫塞尔廷(MichaelHeseltine)、尼格尔·劳森(NigelLawson)、威廉·黑格(WilliamHague)和戴维·威利茨(DavidWilletts),还有卡梅伦内阁中曾经的唐宁街首席顾问史蒂夫·希尔顿(SteveHilton)都毕业于牛津PPE。现任保守党内也有一些牛津PPE人,包括卫生部长杰里米·亨特(JeremyHunt),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PhilipHammond),就业及退休保障大臣达米安·格林(DamianGreen)和司法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ElizabethTruss)。 正准备写书探讨大学系统的前任教育部长威利茨(Willetts)表示:“PPE之所以蓬勃发展是因为英国教育的弊病之一在于过早进行专业细分化,而PPE则更接近美国久负盛名的通识教育。作为一名PPE毕业生,你最终会对现代政治史有广泛涉猎,遍历政治思想与哲学思辨的激流,攻克从货币主义到凯恩斯理论的经济学堡垒。你被逼迫在一学期完成浩如烟海的作业——16篇论文。当你未来需要在截止日期内完成讲稿时,就会发觉受益无穷。”威利茨(Willetts)还表示:“作为部长,你有时会觉得在英国的政治生涯就像攻读PPE时论文危机的无休止循环。” 不是每个人都认可最后关头的临阵磨枪和逢场作戏——不禁想到卡梅伦内阁匆忙组织的脱欧公投——是统治国家的最好方式。去年10月,领导英国脱欧运动的活动家兼前政府教育顾问多米尼克.卡明斯(DominicCummings)在他颇具影响力的博客里写道:“如果您年轻,聪明,对政治感兴趣,学习PPE课程前还请慎重考虑…这可能带来严重的问题,因为它会鼓励像卡梅伦和艾德·鲍尔斯这样的人…一本正经、虚张声势地大放厥词”。 其他关于PPE的评论更刻薄。詹姆斯·德林波尔(JamesDelingpole)去年在极右翼网站布莱特巴特(Breitbart)上嘲讽道:“所有垃圾尾货都在牛津攻读PPE课程”。英国独立党的奈杰尔·法拉奇(NigelFarage)有时会把过于繁冗的政治理念戏称为“PPE式胡言乱语”。在小报和互联网上,PPE已成为精英主义,不切实际,不接地气的代名词。年,专栏作家尼克·科恩(NickCohen)(毕业于牛津的PPE课程)在保守的《旁观者》(Spectator)杂志上发表了自己对这门课程的看法。他写道:“PPE课程培育了自《年改革法案》以来规模最大也最受唾弃的统治阶级独立组群”。 埃德·米利班德、大卫·卡梅伦、菲利普·哈蒙德组图 英国是一个因纵容精英教育而臭名昭著的国家,拥有精密划分的等级制度和紧密联系的权力网。虽说方式上比较粗俗和狭隘,但这些仇视PPE的人正确地指出了这一怪象:单单一个学位,和它造就的思维模式居然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如此之久。而在牛津PPE内部,这些争论正在以更微妙的方式不断回响。保守党同僚斯图尔特·伍德(StewartWood)(艾德·米利班德的前顾问)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了PPE学位,年至年间在牛津教授政治学,至今仍经常负责组织牛津PPE学子的研讨会。他表示:“它仍然活像一门给年统治英属印度的人开办的课”。“每周进行海量阅读;撰写综述论文——这些都是大英帝国晚期公务员的工作。在PPE的政治课程里,你可以在三年的学习中对当代公共政治问题闭口不谈却仍然左右逢源——因为他们总是在不厌其烦地讨论“过去”,讨论政治体制,然而对民粹主义或社会运动的关心却远远不够”。 伍德认为,这门课程的结构本身使许多PPE毕业生陷入某种“中间派的偏见”。“课程涵盖的内容如此之多,以至于大多数学生会错误地认为,实现正义的唯一方法是采取中间态度。他们错误地推断,要想在考试中拿高分,必须避免成为一个显眼的离群者。他们以为如果在各方各面都略知皮毛,就绝不会露马脚。” 自由市场的智囊团——经济事务研究所所长马克·利特伍德(MarkLittlewood)曾在年至年期间攻读PPE学位,他认为该学位的政治偏见正在加深。“PPE课程将人推向某种集权型角色。我的导师绝对极具魅力、出类拔萃,但我认为我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个纯粹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或古典自由主义者。学生的意识形态都势不可挡地左倾”。一位正在攻读PPE课程的学生表示:“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所有在牛津大学教授政治的学者都是自由主义者,从温和派保守党到温和派工党。在经济方面,不少人的观点偏右,但几乎每个人都是社会自由主义者。” 牛津PPE的兴衰是整个大不列颠故事的一部分:兴盛了一百多年的政治权威可能正在不断衰落。伦敦金史密斯学院政治讲师威廉·戴维斯(WilliamDavies)说道:“PPE危机可能是更广泛的社会民主危机的体现之一”。“PPE被看作是国家机构的一部分……与公共服务连接的特权”——现在,相信这一观点的选民正越来越少。正如戴维斯(Davies)所说,PPE毕业生一度被广泛誉为怀揣远大抱负的高素质人才,但现在,他们被看作“妖怪”。区区一个本科学位怎么变得如此重要? 牛津PPE课程在创立之初是前卫的。年,在俄国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学进入了改革阶段。通常故步自封、变革缓慢的牛津大学,根据其官方校史,也在改革中开始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nsiduna.com/jsdjd/5946.html
- 上一篇文章: 从筑梦起航到精彩亮相世界技能舞台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