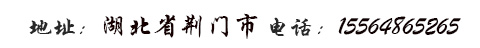女王案牙买加文学你了解一下
|
哪里看白癜风的医院好 http://baidianfeng.39.net/a_zhiliao/150911/4694665.html 《女王案:当代牙买加短篇小说集》展示文学新兴力量 自年牙买加作家奥利夫·塞尼奥尔首次获得英联邦作家奖以来,牙买加文学在全球文学场域内越来越为人瞩目,逐渐从“加勒比海文学”中分离出来,进入国际读众的视野。 塞尼奥尔以她的短篇小说集《夏日闪电》打败了比她知名得多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和本·奥克利。这场备受瞩目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牙买加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文学产出,在此后的三十年中掀起了一股高涨的文学热潮。 近日,《女王案:当代牙买加短篇小说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了包括塞尼奥尔、麦肯齐在内的9位牙买加知名作家的10篇小说,主题包括移民、社会动荡、后殖民、底层人民的生活等。全面反映了牙买加的社会状态和人民生活的境况,令人得以一窥多元混融的牙买加小说。10月28日,牙买加英联邦作家奖得主、《女王案:当代牙买加短篇小说集》主编阿莱西亚·麦肯齐来到中国,与《女王案:当代牙买加短篇小说集》主编、译者陈永国对谈,解开牙买加文学的多层迷雾,重新审视牙买加文学的历史与发展及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 阿莱西亚·麦肯齐介绍说,牙买加和中国之间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早在加勒比地区以及大英帝国殖民地的奴隶制被废除时,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工人就进入加勒比地区开始工作。所以在这两个地区有很强的血脉联系,这种联系已经有很多年。《女王案》九位作者中的其中一位就是有中国血统的,维克多·张,是西印度大学的一位文学教授。 从写作者的角度而言,阿莱西亚·麦肯齐说,“牙买加的很多作家都受到英国文化的影响,因为牙买加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英国的殖民地。从年牙买加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之后,牙买加一直在构建、强化自己的身份,但是英国文化对我们的影响还是很大,这种印记难以磨灭。牙买加人因为自己是牙买加人而感到骄傲,我们有一段艰难的历史,但是我们通过努力生存了下来,拥有了强大的文化。当我写作的时候会更多的想到牙买加的历史,比如奴隶制,比如殖民地的历史,但是同时我也会想到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取得了多少成就,我们给予世界的呈现和风貌。”有趣的是,阿莱西亚·麦肯齐的儿子女儿都在学习中文,这也促成了这本小说集率先在中国出版。作家与出版方都表示,希望有更多的作品能与中国读者见面。 《女王案:当代牙买加短篇小说集》 [牙买加]阿莱西亚·麦肯齐[中]陈永国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女王案:当代牙买加短篇小说集》简介: 自年牙买加作家奥利夫·塞尼奥尔首次获得“英联邦作家奖”以来,牙买加文学在全球文学场域内越来越为人瞩目,逐渐从“加勒比海文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分支进入国际读众的视野。本书的出版是牙买加在国外出版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将在牙买加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本书结集的10篇小说,都是当下活跃在牙买加和加勒比海文坛著名作家的代表力作,作家包括现代牙买加文学运动的开创者奥利夫·塞尼奥尔、阿莱西亚·麦肯齐(曾获英联邦文学奖)、威尔玛·波拉尔德(曾获美洲卡萨德奖)等。他们都笔耕不辍,为加勒比海文学和世界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女王案:当代牙买加短篇小说集》主编简介: 阿莱西亚·麦肯齐(AleciaMckenzie):牙买加作家、画家和记者,居于法国巴黎。她的第一部专著《卫星城》和第一部小说《甜心》均获得英联邦文学奖,年曾入围英联邦短篇故事奖。其他著作包括《院子里的故事:那特兰雨停之后》和《医嘱》等。她的短篇小说已分别译成荷兰语、西班牙语、波兰语和芬兰语。 陈永国: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名人推荐: 这是一群活跃在加勒比海文坛的知名作家的作品,内容涉猎广泛,故事情节隐秘曲折,属于真正的后殖民故事。 ——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北京外国语大学前副校长金莉 这本书,将遥远的加勒比、遥远的牙买加送到我面前,于是我有幸读到了另一种英语小说——激情、悲伤、纯洁,都如此浓郁,令人欲罢不能。 ——当代著名作家李洱 《女王案》节选 奥利夫·塞尼奥尔著 每天下午四点钟前,舅舅准时出门。他不需要做什么准备。自从英国回来后,他那三件套就未离过身,所以,他所要做的只是戴上圆顶礼帽,拿上拐棍和手套。但是,即使这些简单的动作也浸透着伟大的目的性和深思熟虑。舅舅做每件事都如此。帽子的角度要正确,手套拿在右手里,要与手杖构成准确和谐的关系,然后举步外出。 “下午好,小丫。”他会用一种深沉悠扬的声音招呼我。 “下午好,舅舅。”我说,边从我正在学习的卧室里出来,望着他启程。 舅舅僵直地走下三个水泥台阶,走上通往大路的小路,从不错过一个节奏,我肯定他行动准确,仿佛在皮卡迪利马戏院里散步一样。唯一的差别是乡间大路没有人行道,事实上,那并不是什么路,只是铺着石头和泥灰的小道,也没有排水系统,所以,路两边都是深沟,每次雨后沟里都积满了水。路上没有行人车马是好事,因为唯一可以散步的地方是路中间。 舅舅对此毫不在乎。他会走在路中间,摇晃着手杖,也不管尖利的石头是否会扎破他那双擦得锃亮的英国鞋,或者灰土路上的灰尘会不会粘在衣服上。他迈着僵直而准确的步伐,走一英里半到村里的广场,每遇到一个人都会脱帽致意,并致以从不改变的微笑,因为那笑就固定在他脸上,永远是内向的。有时,如果我碰巧也在广场,我会在那里与他偶遇。他会在路边散步,准确地在街角转弯,走到路对过儿,顺着另一边的路朝家的方向走去,并微微摇头婉言谢绝酒吧里的那些人—姥爷的朋友们—让他进去喝两盅的邀请。舅舅只是笑一笑,点点头,然后接着走他的路。他散步时从不和人说话。 舅舅走路如此挺直,他总是和我说起我曾经拥有的那个上发条的小玩具人,它的手和脚都机械般地一挺一挺的。有时候他也感到自己僵硬,甚至坐着也是。我从来没见过他舒缓过,谁也没有见过他脱过他的三件套。 舅舅刚从英国回来的那几天,没有人对他的行为多加考虑。大家都知道他离开二十多年了,需要时间重新适应环境,都期待着一旦摆脱那种僵硬和怪异,舅舅就会和正常人一样了。开始的时候,姥姥曾试着让他脱掉西装、背心和领带;她想象穿着那些沉重的、黑色的英国毛料衣服还不得热得开了锅,虽然他带回来一个行李箱,但除了睡衣、一件袍子、卫生用具、一把好看的梳子和牙具外,箱子始终原封未动地锁着。她曾主动提出帮他整理东西,晾晒衣服,需要熨的也帮他熨熨。“不,谢谢,妈妈。”他说。姥姥确实主动把他父亲的棉纱衬衫和咔叽裤子、还有一双鞋拿出来让他穿,因为他们穿相同的尺码,以为他没有热带服装,但他还是说,“不,谢谢,妈妈。”也就仅此而已了。他说话的声音圆润悦耳,那么文雅,那么简练,我觉得他措辞时嘴里总是含着一颗熟李子。“不,谢谢。”这就是他所说的一切,但甚至这我也喜欢。 “给他点时间,让他重新适应我们的生活,”我听到姥姥每晚上都和姥爷说,“很快就会正常的。” 姥爷不回答。除了星期五晚上去拉姆塞酒吧喝白朗姆酒的时候外,姥爷平时不怎么说话。可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开始唠叨个没完没了,甚至让人烦,有时还听到和他的朋友安德森先生大声争吵,深夜里两个人喝醉了酒,在大街上踉踉跄跄地吵嚷着。隔着墙我能听到姥姥(总是躺在床上听外面的动静)大声地叹气。我能想象她边摇着头,边下床把油灯捻亮。姥爷出门后她总是把灯调得暗暗的。我能从门缝里看到灯光突然亮起来,听到她急忙回到床上,这样姥爷踉踉跄跄进屋的时候她就能假装睡着了。星期五夜里她从不对姥爷说什么,因为除了这一晚,姥爷实在没什么可抱怨的。“已经不是我们年轻的时候了。唉,孩子。”她会说。“那个男人每天都让我哭得泪流满面。”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姥爷变得柔和了,现在几乎不说话了。舅舅也不说话,除非有人对他说话。而不管对他说什么,他都回答说:“不,谢谢。” 我是唯一一个舅舅可以多说几句话的人,我从来不知道为什么。姥姥对我说,他离家之前曾经和妈妈很亲密,而我又简直和妈妈长得一模一样。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原因,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去世了,姥姥只有她的一张照片,还是一张快照,她那么苍白,那么疲倦,我都看不出她的面目特征来。有时候,我想舅舅是不是以为我是他去英国时留下的小妹妹,因为他也叫她小丫。 舅舅回来和我们一起住的那年我十岁。我对他极其好奇。他僵直地坐在阳台上,我总是不离左右,希望他能对我说点什么。他整天坐在阳台上,脸上带着那种神秘的微笑,在姥姥来召唤他吃饭之前,他从不放松一下身体。然后,他会来到餐桌旁坐下来,假装吃饭,因为几乎没有什么食物碰过他的嘴唇。 长时间以来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注意到过我。一天下午,我路过他门口的时候,惊讶地听到他喊我:“过来,小丫,听听我的心脏。” 我感觉有点难为情,就走过去把耳朵贴在他的胸口上。 “听到什么了吗?”他问。 “它在跳,舅舅。”我说,除此之外我还能说什么呢? “不,小丫,你错了,”他说,“你听到的不是我心脏的跳动。我早已没有心脏了。那是他们装在我身体里的机械装置。像钟表一样嘀嗒地响。我在那里住院的时候他们把我的小心脏拿出去了。医生们把一些电线接在我头上,乘我失去知觉时把我的心脏拿出去了,装入了这台机器。我从来没有让他们这么做,小丫。从来没有。这是最高级的犯罪。我给女王写信谈及此事。我给女王写了四十封信。你知道女王回信是怎么说的吗?” 他在等待回应,所以我诚实地回答说:“不知道,舅舅。” “小丫,女王回信说那不是她该管的事。她这么说你同意吗?她难道不是所有人甚至最卑贱之人的女王吗?我们不是口袋里揣着带着她头像的钱币到处走吗? 全世界不是有数亿人口袋里揣着她的头像到处走吗?可她却说这不是她该管的事,她的医生、医院—皇家,外面用大大的字母写着的,每一个人都看得见— 她的医生拿走了我的心脏,把一口钟装进去了。你认为这是对的吗,小丫?我连喝水都要特别注意。我的整个余生都要特别注意。万一他们装在里面的机器生锈了呢?但我没有放弃,小丫。如果我必须终生寻求正义,我就要寻求正义。总有一天我要让你看看我和女王的全部信件。” “好的,舅舅。”我说。 舅舅从假兜里掏出表,看了看,恰好差一分到四点,于是他戴上帽子,拿起手套和手杖。“下午好,小丫。”说着又去散步了。 孤独图书馆:你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我的孤独是一座天堂。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nsiduna.com/jsdjd/8390.html
- 上一篇文章: 世界地理终极总结2
- 下一篇文章: 牙买加华人群体是怎样帮助雷鬼乐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