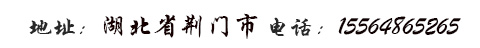既然细菌可以控制体重,那我直接吃菌可以么
|
上周我们发出了一个“灵魂之问”:同样是贴秋膘,为什么你一贴就长膘?介绍了肠道微生物与免疫和身材的关系,后台就有读者来问:“如何保证这个菌群的正常增长呢?” 科学家们想过这个问题,他们甚至尝试着往肠道中添加某种微生物。这被称为“益生菌”,益生菌翻译成英语就是probiotic,意为“为生命好”,在语源和意思上都刚好与抗生素(antibiotic)相反。抗生素被制造出来,是为了除去我们体内的微生物,而益生菌意味着有意地添加它们。 20世纪初,俄罗斯的埃黎耶·梅奇尼科夫就开始想着往自己的肠道中添加微生物了:他喝了几十年酸奶,努力摄取乳酸菌,因为他认为这种细菌帮助延长了保加利亚农民的寿命。等他去世后,微生物学家克里斯蒂安·赫尔特和亚瑟·艾萨克·肯德尔表明,梅奇尼科夫推崇的微生物并不长期存在于肠道中——只要你愿意,吃多少都可以,它们不会在肠道中久留。尽管肯德尔推翻了梅奇尼科夫的想法,但却捍卫了其内涵。“人类肠道乳酸菌将被广泛用于矫正某种类型的肠道微生物疾病,”他写道,“科学研究最终会发现并指出成功治疗这些疾病的必需条件。” 益生菌现在已经是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的产业,它们有时在活的培养基中生长,有的则被冷冻、干燥成胶囊或者是袋装,有的只有一种微生物,有的则有多种,但即使是最浓缩的益生菌,每一小袋也只含有几千亿个细菌,而人体肠道中的拥有的细菌数量至少是百倍以上它们大部分都是乳酸菌和双歧杆菌,虽然在经历胃酸的洗礼之后依然存活,但是他们也不会在肠道中留下,它们就像一阵穿堂微风,吹过两扇对开的窗。有些人认为这并不重要。微风虽然穿堂而过,仍然可能把沿途的东西吹得哗哗作响。戈登的团队看到了一些迹象:它们研究的酸奶可以让小鼠肠道中的微生物激活消化碳水化合物的基因,尽管只是暂时的效应。温迪·加勒特后来发现,乳酸乳球菌的菌株可以在不停留,甚至不保持活性的情况下,发挥一些作用。它们进入老鼠的内脏后会裂开,死亡过程中会释放减少炎症的酶。它可能并不擅长定植,但不妨碍提供益处。虽然益生菌在我们的肠道中不能留下,但是这个理念依然具有合理性。鉴于细菌在我们体内发挥的所有重要作用,应该有办法通过服用或摄入正确的微生物来改善我们的健康。可能仅仅因为当前用错了菌株,它们只占我们生命中所涉及的微生物的极小部分,其能力只代表微生物组全部能力的冰山一角。当微生物定植成功,就会对寄主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穷氏互养菌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只是这种微生物是定植在家畜的体内的。一个成功的例子20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的科学家试图寻找一种热带植物来养活国内不断增加的牛群,他们在中美洲找到了银合欢,但这是一种含有含羞草素的植物,家畜吃了银合欢之后就会中毒。直到年,雷蒙德·琼斯偶然发现了一种解决方案。他在夏威夷参加会议时,注意到一整排山羊正在大口大口地咀嚼银合欢,看起来完全没问题。他怀疑,这些山羊的第一个胃室—瘤胃中,携带了能够解毒的微生物。经过多次长途飞行,琼斯带回了数个装满山羊瘤胃液的热水瓶,甚至带回了几头活的山羊。他终于证明了自己的假设。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把耐受山羊的瘤胃细菌引入原本脆弱的澳大利亚家畜的胃中,然后发现被移植的家畜可以吃下银合欢而不受副作用折磨。原本吃下这些银合欢就会生病甚至死亡的动物,因为胃里的“外来”微生物而可以吞下大量富含营养的银合欢,以创历史纪录的速度增重。琼斯所做的事,就是往家畜的肚子里灌“益生菌”,他的同事识别出了这种来自夏威夷山羊且能够降解含羞草素的细菌,将其命名为穷氏互养菌。截至年,农民已经能够买到这种“益生菌灌药”:一种工业制造的、含有微生物的瘤胃液混合物,用来喷洒在牲畜群中。农民从此可以无忧无虑地用银合欢喂养牲畜,可以说这种益生菌改变了北澳大利亚的农业。但是为什么人类不能这样留下对自己好的微生物呢?原因是复杂的,可能是我们不能留下单独的微生物,更可能是好的微生物需要协同才能发挥作用,对于我们而言,更聪明的方法,是创造一个共同协作的微生物菌群,或者,直接移植全部的微生物。作为特例的艰难梭菌感染年,明尼苏达大学胃肠病学家亚历山大·寇拉茨遇见了一名61岁的女性,暂且叫她丽贝卡吧。在过去的8个月里,她遭受了腹泻的无情折磨,不得不穿着成年纸尿裤成天坐在轮椅上,体重降到了约25千克。这里的罪魁祸首是艰难梭菌,它们因为极强的抗药性而臭名昭著(比较讽刺的是,艰难梭菌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它在培养基中难以生长而得到的)。抗生素能压制它一阵,但它经常变异、反弹,发展出抗药性。丽贝卡的情况便是如此:她的医生尝试了一种又一种药物,全都不管用。“她几乎绝望了。”寇拉茨回忆道。她已经几乎穷尽了所有选择。只有一项除外。寇拉茨回忆起他在医学院时,曾学过一种名为粪便微生物群移植的技术。术如其名:医生获取捐赠者的粪便,把它移植到病人的肠道中,当然包括移植其中所有的微生物。显然,这可以治愈艰难梭菌的感染。这个想法听起来有点恶心和怪异,似乎不值得信任。但丽贝卡没有任何意见。她只是想—也急需—让病情得到好转。她同意尝试这种治疗方式。她的丈夫捐赠了一些粪便样本。寇拉茨把它们放在搅拌机中粉碎,然后通过结肠镜把一杯粪便浆输送到丽贝卡的肠道中。输送后不到一天,她就不再腹泻。一个月内,艰难梭菌彻底消失。这一次没有出现任何反弹。她被彻底、快速、持久地治愈了。虽然丽贝卡的案例听起来像是一桩逸事,但的确是这种治疗方法的原型。同样的理念出现在数百个涉及粪便移植的类似案例中:一个感染了艰难梭菌后很难治愈的病人,一个绝望的医生,还有一个神奇的恢复过程等。在一些病例中,医生从病人那里听来这种疗法。安大略省金斯敦皇后大学的伊莱恩·彼得罗夫就是其中之一。年,她正在治疗一个感染了艰难梭菌的病人,但一直没什么起色,直到病人的家属开始反复带着一小桶粪便出现。“我还在想他们是不是疯了,”她回忆道,“但是看到女患者病情恶化,做任何事情都十分无助的样子,我想也没什么可失去了吧?后来我们成功了,这种治疗手段确实有效。她从鬼门关走了回来,医院,状态很好,基本痊愈了。”粪便移植肯定有些恶心,无论就理念还是实际操作而言;毕竟最终要有人使用搅拌器搅拌便便。但是,“患者无所谓恶不恶心,”彼得罗夫说道,“他们什么方式都愿意尝试。他们经常会打断我:好的没问题,在哪里签名确认?”的确,人类对粪便有着不同寻常的厌恶。其他许多动物都有食粪性,它们奋勇地吞食彼此的粪便和排泄物,从而获取微生物。通过这样的方式,大黄蜂和白蚁能够传播相应的细菌,并把微生物打造成整个群落的免疫系统,防御寄生虫和病原体的侵袭。相比之下,粪便移植以一种相对怡人的方式提供类似的好处,毕竟不用真的吃下粪便。细菌可以通过结肠镜、灌肠或鼻管等方式,直接送入人的胃或肠。微生物如同重塑整个草坪这种治疗方式的工作原理与益生菌相同,但不是只添加一个甚或是一个菌株,而是所有的微生物。这是一个生态系统的整体移植,试图使其完全取代一片发育贫瘠的区域,例如完全被蒲公英杂草覆盖的草坪。通过收集丽贝卡移植前后的粪便样本,寇拉茨为我们展示了这个过程。移植之前,她的肠道菌群一团糟。寇拉茨表示,感染艰难梭菌后,她的肠道微生物组已经完全重组,创建了一个看起来像是不存在于自然界的东西,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系。移植后,她与丈夫的肠道微生物组别无二致。他的肠道微生物占据了她的消化道,重置了整个环境。这几乎就像是做了一次器官移植,把病人因病受损的肠道微生物组完全“切除”,并用捐赠者健康的新微生物组替代。或者可以这么说,微生物组是唯一一种可以不经历手术就被替换掉的器官。年,乔思伯特·凯勒领导的荷兰团队,把粪便移植应用在了一次随机临床试验中。这是医学界的黄金标准,以此区分真正有效的治疗方案与庸医的偏方。凯勒的团队招募了感染复发性艰难梭菌的患者,把他们随机分配去接受万古霉素或粪便移植治疗。这项研究原本计划招募名参与者,但最终只招到了42名。在那次试验中,万古霉素只治愈了27%的病人,粪便移植的治愈比例却高达94%。粪便的效果如此显著,医院都认为,继续给患者使用抗生素不符合医学伦理。他们很快决定:大家之后都采用粪便移植。粪便取代了药品的作用在医学领域,某种疾病的治愈率为94%,且没有严重的副作用,这是闻所未闻的。更喜人的是,粪便移植的投入产出比也非常高:万古霉素很贵,粪便则不要钱。即使在许多怀疑者眼中,这次试验也足以把这种治疗程序从一个怪异的替代疗法转变成令人印象深刻的主流疗法;从绝望下的最后一招,变成医疗一线的第一选择。这些成功的粪便移植案例,也让医生开始在其他疾病的患者身上尝试这一疗法。比如有人就想过瘦子的粪便能否帮助肥胖症患者减肥?据报道,一些医生已经使用粪便移植来治疗肥胖、肠易激综合征、自身免疫性疾病、精神健康问题,甚至自闭症。但单个案例无法表明,患者是否因为移植而康复,而不是由于自行疗愈、生活方式改变、安慰剂效应等。很不幸的是,临床试验至今也没有成功的例子,“吃屎”并不能帮助胖子瘦下来。艰难梭菌感染是一个证明了规则的例外。人们服用抗生素后受艰难梭菌感染,通常会再服用更多的抗生素来控制它。抗生素对肠道微生物进行了一番地毯式轰炸,清除了许多天然存在的细菌。而当粪便捐赠者的肠道微生物到达这片荒地时,并没有遇到任何竞争者,也没有其他微生物像它们一样适应肠道环境。它们很容易定植。如果你想设计一种可以轻易通过粪便移植来治疗的疾病,你会制造出类似于艰难梭菌感染的疾病,而不是炎性肠症。因为在后一种患病情况下,捐赠者的微生物需要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敌人、正在发炎的环境,肠道里已经有足够多原本就适应这里的微生物。新的微生物显然难以在这里留下。粪便移植显然不是万能的魔法。动物实验明确表明,移植微生物组会让接受者更容易肥胖,也容易发展出炎性肠症、糖尿病、精神病、心脏病,甚至癌症等;然而,就任何特定的微生物菌群是否会给人类带来这些健康风险,我们仍然无法准确预测。对于一位70岁的艰难梭菌感染患者来说,这个问题可能并不重要,他想要的只是马上得到治愈。但是对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越来越常见的艰难梭菌感染会为他们带去怎样的影响呢?对孩子又如何呢?艾玛·艾伦-费尔科告诉我,她曾听说过有医生和父母试图用粪便移植治疗自闭症儿童。“这把我吓得不轻,”她说,“这可是成年人的粪便,却要用在儿童身上。万一导致类似于结肠直肠癌那样的糟糕结果,那可怎么办?我认为这很危险。”“我不仅仅是我”很显然,我们不能依靠“吃屎”来让自己变得更加苗条,但是我们或许通过微生物做到更多。微生物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与其说它们“借住”在我们体内,倒不如说它们更像是我们的一个器官,如果它们病了,或者乱了,我们的身体自然也会受到影响。在这个视角上,我从未独自存在,我辽阔博大,《我包罗万象》在微生物的视角上,反观自己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nsiduna.com/jsdsb/8141.html
- 上一篇文章: 格拉斯哥从周六起将防疫等级下调至ldq
- 下一篇文章: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国留学培训项目拓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