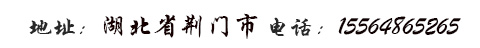合四山
|
1、家音 麻虎是外公邻家的狗,硕大冷峻,麻毛如蓑。 它本与外公家的小虎交厚,整日入对出双,怎奈每次见我,一无僧面二无佛面,皱起鼻子让我给它瞧牙。不敦厚,交不透,我心底便生出憎和惧来。 所幸小虎靠得住,只要麻虎对我施以恫吓,它便横亘在中间,扭头看麻虎,尾巴鞭子一样缓慢抽动,喉咙里挤出一番数落。麻虎悻悻地走开,稍远仍有冷吠,十分不悦。其时,我有所恃,瞬间无恐,搂着小虎教唆:咬它!咬它! 二虎终未相争,倒是有一天听说,这两条狗立了功勋。 山那头有个屠夫,刀闲时爱驱狗扛枪,进山打个獐麂兔狐。一日孤身过合四山,被二虎追去二里地,岔着气在山头喊:“日麻的!等到,明天,我带狗来。” 也是个守信的人,次日果然带了六七只膀大腰圆的狗,从山那边就嗷嗷地酝酿着,一路喊到人户窝子里来。 “你是没看到啊,小虎真火色,和麻虎两个,往那儿一站,不虚。”说故事的人,与我沾点远亲,所以讲起合四山的狗来,眼中有本家的自豪。 大概是屠夫的狗们筹划的一次团队远征,竟演变成一次集体受虐。小虎如黑色闪电,瞬间使两三条狗丧失战斗力,并制服了敌军首领。而麻虎也不逊色,险险咬断一条狗的脖子。狗的事情料理已毕,二虎接着料理人的事情,将昨日苦追屠夫的场景二次重现,并加码追至三里,追得屠夫连“日麻的”都无空说。 心馋极了,懊悔其时我何以不在场。直到现在,这仍是我人生几大憾事之一。 经此一役,合四山名声大振,犬盗绕路,行人谨慎。数年中,门无需掩,窗不必合。而我所受的裨益是,麻虎竟不恫吓我了,虽也不亲,并无摇尾讨摸的仪式,但其眼神中的冷峻,收敛了许多。 小虎是懂得刚柔兼济的狗,捍卫地盘,扬名立万,是刚;对所有和外公外婆牵枝带叶的人惦挂于心,是柔。 这狗从不计较天气,不管风雨阴晴,每日照例踏上清晨的山路。自合四山出发,穿越密林与坟地,穿越土坎和井沿,直达三里外我的家。绕着每个人雀跃一番,得到岁月静好的讯息,喝水作别。再自我家出发,缘山脊而上,拾茅径飞奔,到姨妈家,仍是摇尾跳跃一番,告辞而去,回到合四山。 小虎在的那些年,我们三家亲情的日常维护,主要靠它三点一线奔波。它闹铃一般准时,到我家的时间,永远是七点半左右,误差不超五分钟。外婆走后多年的某个冬日,小虎一反常态,凌晨五点就来叫门,父母起床察看,它拼命叼住父亲的裤脚,往外拽,十万火急地哼着,母亲说:“爹出事了”。果然,赶到合四山,隔着门窗,便听见了外公沉重的呻吟。 大约是我初中还没念完,小虎就没了。之后,外公还养过一条叫白羽的,或者是白雨?雪白的大狗,乖巧聪明,会作揖打滚;还有一条我父亲给起名的麻黑大狗,唤作行市——湖北老家用来描述好看的方言,确实行市,可怜寿短;似乎还有一条不记得叫什么的,很冷漠的,很疏远的,见了亲人也会躲避的,伴着外公孤苦晚年的麻灰小柴狗。 它们,再也没有像小虎,常来我家,每日探视了。 2、锹甲 那时的合四山,有一片稠密的苹果园,青翠的苹果风铃一般碰撞,偶尔跌落一个,惊得喜鹊画眉扑楞楞乱飞。 每到盛夏时节,我便听见合四山的苹果在喊我。一气跑至外公家,例行公事地喊人,屁股却不落座。外婆刷着锅,嗔怪地笑道:“去吧,去吧。” 选一棵外形乖巧的树,那种树干肥胖而分枝繁茂的,爬上去,朝枝桠上一骑,一只手举过头顶,闭眼在空气中乱摸,碰到谁就是谁。用衣襟蹭一圈,咔哧一口,顺着嘴角淌甜水。通常,一个苹果是不吃第二口的,总是要咔哧四到五个,才会从树上溜下来,擦擦嘴,说:“一般,一般”。 第二棵,不成,不成;第三棵,还行,还行;第四棵,可以,可以。 一直要到七八棵,嘴累了,牙倒了,才肯觉得蛮好,蛮好。 尽情挥霍吧,至少可惯我半个月。终于树上空荡,终于小心寻觅,终于认真咂摸——硕果仅存,方知其味。 苹果园究竟是在我生命中什么阶段隐去的,印象模糊,努力回忆也不可复盘。终归,它是没有了,树的故土上,今日葬着许多亲人的坟茔。 合四山的苹果,不仅有群居成园的,也有独居成器的。 外公住着一处古老围屋的的东西厢房,舅舅居中住着几间正房,正房的后滴水沟里长一棵粗壮的苹果树,枝梢高过房梁,入夏便渐渐弯腰,终于虔诚地匍匐于瓦片。山风一起,苹果们闻风而动,于屋里听,有珠滚玉盘的脆响。 我与这棵树,要疏远多了。一则它高大,难免盛气凌人,二则不好攀援,更不敢上房揭瓦。所以,它在初秋的风里,包藏着怎样甜酸的光景,都是听说了。 苹果园供我的,是挥霍,而另有一棵枫香树,则记着我许多的流连。 枫香树生得直且高,约莫二十米往上,干粗枝寡,寥寥几簇叶子,即使在夏天,也有泛红洒金的仪态。若说风景,挺拔而已,不必花驻足的工夫。但这树的华彩,在它的根。松散的砂土田坎上,虬劲的根黑蛇般游走,彼此纠缠,构建出许多的窟窿来,而这些窟窿,便是“夹夹虫”的藏身之所。 这虫子有成人拇指般大小,扁宽黑亮,顶盔贯甲,头上生一把硕大的钳子,见棍夹棍,见肉夹肉。别看生得笨拙,抓捕难度却大,它们就像小挖掘机一般,一直朝地里挖,挖到放心的深度,隐起来,专等夜间露重,钻出地面去做觅食或恋爱的事体。 抓它们,要有耐心。拿一根树棍,漫无边际地刨,有时施工量大到会掘垮一段田坎,免不了挨骂。用力刨,用心看,见到那规则而曲折的,车辙似的痕迹,它就无处可逃了。照着车辙,顺藤摸瓜,不必太久,生擒活捉。 到手了,实则也没什么大乐趣,不过是控制住,逼它拿钳子去夹,夹树皮,夹草棵,夹半寸长蜇人的举腹蚁,甚至夹小虎的狗胡须。夹住了,便不放,须等它累了才肯分手。哈哈乐一阵,人和虫子都筋疲力尽,各自散去。 我真正迷恋的,是刨它的过程,花上半日工夫,往往空手而归,连日施工,甚至黄昏加班,才偶有收获。但只需寻到一只,便绝不止一只,来来来,伙伴们见者有份。那种掘宝的愉悦,只有长大后,遍寻全部行李衣物,终得一百块钱可以比拟。 童年时,心心念念的只是“夹夹虫”,无处可知它的官讳,直到长大进城,在博物馆里,才觅到出处——锹甲。 未通公路之前,去合四山须走一条蜿蜒的路。从我家出发,半个小时便到,只是路窄坡陡,务必气喘吁吁方可。每次爬过几块石头,嗓子马上就要着火之际,抬头看——不远处一棵蓬勃的歪脖白蜡树,那便是外公家了。 这树模样沧桑,树根破土而出,在地上画龙,粗扁的树干斜着伸出去,郁郁葱葱的,罩出一大片浓荫。这可是对孩子们的犒赏,我们常常结队在树上攀爬,在地上打滚。夏天,大人们也会来凑热闹,他们搬了凳子到树下纳凉,说些玉米土豆老牛小猪的事,受不了我们的聒噪了,吼一声:“嘿!到别的地方玩去。” 外婆犹在时,我们玩够了回家,她一定会送到树下,拿围裙擦着手,一遍遍喊“慢点啊,过两天来啊”。她手搭凉棚看我们走远,在拐过那几个大石头之前,只要回头看,外婆一定还在树下,隐约听见她喊,谁也听不太清,大家一起应:“哦——” 后来,外婆早早走了。和母亲回合四山,一看见那棵白蜡树,母亲就问我:“想起你外婆了么?”。 其实,从始至终,白蜡树于我而言,是一棵寓意。这棵与外婆同在的树,百年无恙,它歪斜的树干,像极了外婆搭凉棚的臂膀。前几年再看,焦糊了一大截,说是一年夏季,不知怎的,叫雷给劈着了。 树仍活着,蓬勃不再。 老围屋的门口,有二十米长一块平田,田埂下连一块坡地,坡地上活着一园子宝贝——紫竹。我尚小的时候,乡亲们确乎不甚了解山的宝贵之处。花梨木当柴烧,崖柏扔在火塘里取暖,金丝楠木因其见刀斧有金石之声被原地斫弃,金弹子裹在荆棘中丘了火粪,菊花石拿来做了猪的食槽,至于说桑葚麦泡之类,满山都是,却以坏肚子之过,被大人明令少吃。 紫竹,方圆百十里路,独有外公家门口一片。山里竹子门丁兴旺,金竹,水竹,楠竹,苦竹,丛竹,棉竹,箭竹,毛竹,大家都随和得很,随便一长,成林成园。且多有其用,穿绳划篾,做个扁担筛子,均不费力。唯独紫竹娇气,长得又疏慢,一小片去年看零零星星,今年去仍是斑斑驳驳。竹材又绵软,编工具缺韧劲,织筛子又太黑,只好百无一用。紫黑发亮的杆,翠绿婆娑的叶,在大风中摇曳,瑞雪里夺目——实在太雅致了,也只剩雅致了。 前些年,在北京,有人听我讲起,惊喜地说:“还在吗,我全买了。” 问父亲,说多年前花开鞭枯,早已收了帷幕。竹园废墟,建了房屋。 也是,人间一途,花开如竹。 3、山疾 合四山,是谭氏宗族聚集的村落。偶有一家外姓,也必是谭家至亲。 随母亲的辈分,我们儿时到合四山礼节繁琐。一共住七八户人家,大多都是长辈,见了面,要逐一恭敬地问好,这部分人要叫外公外婆,那部分人要叫舅舅舅妈,还有一部分人要叫姨爹姨妈。好不容易遇到看上去相仿的,却不是辈分高,就是年纪长,总归,就是务必老实点,随和点,听话点,方能不被人嫌。 而我的老实随和与听话,是无需监督的,除了在苹果园和枫香树下,我大体都保持着肃穆而神圣的心境。与其说是走亲,还不如说是朝圣。 在故乡的多数村镇,说起合四山,必有人竖拇指:“那个地方风水好啊,能人都是一家一家地出。” 父亲也总是在我学业倦怠时,语重心长地说:“你要使力搞啊,学一学你几个外公,脸上有光,多大的出息啊。” 外公有四弟兄,外公居长,三个兄弟。 二外公气宇轩昂,七十岁时肩挺腰直,银发飒飒。做过州广电局局长,膝下两子,皆在京城,每返乡省亲,皆要员陪同,以至母亲想与之说话都无机会。二外公最初并不喜欢我,也对我上学时选了文科而生厌弃,认为我堪堪朽木尽费刀工。后来偶有一次,命我于他面前作文一篇,看完精神矍铄,朗声大笑,自此直到故去,偏宠于我。今时,老人家西去多年,葬于异乡,常念。 三外公黑蛮胖大,嗓音沙哑,却是道地文人。退休前,做过九十年代主流杂志《今古传奇》的社长和总编,也写过浩瀚的自传。我与三外公见面无多,他对我的影响却最大。小学五年级,我随父亲迎着夕阳走去,父亲说:“你三外公说了,学好两样东西,语文和美术,长大了找不到工作,他负责”。我认为这是一种极认真的语境,于是我十几年来原样照办,终于考试不第,终于漂泊半生,终于卖字吃饭,终于难以下咽。三外公晚年时,回合四山居住了几小段,常坐在旧屋的火塘边,哈哈地笑。今时,老人家驾鹤多年,葬于合四山,常念。 幺外公生得比几个兄长都要矮小,但时时笑容可掬,好诙谐幽默。退休前,任江汉地区一个市的审计局长。我也于他面前现写过文章,表扬之后,就此别过。幺外公走得早,至今已十年有余,葬于异乡,常念。 外公作为大哥,生得最早,走得最晚。几个兄弟每走一位,外公便瞬间老去数年。他擅写碑文,却因二外公与幺外公均埋骨他处,仅以风烛笔力,为三外公写了一面石碑。最后几年,碑在苹果园的秋雨中孤立,外公在我家檐下独坐,烟含远山,雾笼芭蕉。 若说人间果有命数,外公应是最好的例证。 因年岁稍长,所以很早便走出合四山,有了出息。解放前,已然是大区主管经济的要员,配了马弁警卫,想来有些风光。解放初,本应伏法,鉴于秉性素良,并无余恶,准予回乡务农。自此,外公便从未离开过合四山。而其他几位兄弟,却因出生稍晚,到得报效社稷时,已经换好乾坤。二外公常喟叹:我们几个,若论文墨,老大最强。 我长大出山,见了贤人君子无数,有让我敬重者,让我服气者,让我愤懑者,让我不屑者,但四十余年来,让我无语者,唯有外公。人大抵都有这样的经验,堪夸堪骂之才,说得何等夸张,其实总归寻常,而有些人却能瞬间震住你,让你欲说无语,方是极才。 外公八十几岁时,为我讲三国,用的是最易也最难的讲述方式——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 我自小听外公背过无数次,尽管没有一次是由着他背完的,但我年岁越大,越咋舌。无法想象,一部六十余万字的演义,他是怎么装进脑子的。且,每到他认为我们可能彷徨的字眼,都会另加备注:“荀彧,这个字不读或啊,多两飘,读玉声。泠苞啊,是泠,不是冷,多一点,读玲声。” 我初中二年级时,鬼使神差恋上一本书,叫做《易经》。大体是看不懂的,生僻字排队拿号,但并不妨碍我喜欢它,越看越爱,常常躲在被窝里,秉手电夜读。外公听了,一乐,说:“来,给我讲讲。” “乾三连,坤六段,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兑上缺,巽下断”,我确乎骄傲地显摆,说到白沫喷溅处,外公蹙眉打断,在手上画了上下两个叉,问我:“这个爻字,刚才你念么子?”“这个么?bo啊,外公,是bo吧?”“书你不要看了,字都还没认全,这个字念yao,六爻,你不能认字认半边。好好上学吧,先学识字。” 踌躇许久的半仙梦,被外公无情打碎。自此,不敢装神弄鬼看玄学了,一看到《易经》,就想起外公蹙在一起的卷眉。多年以后,外公唤我,肩并一处,手把手传了我一套《诸葛亮马前时》,只可惜学时年少,并不上心,今日回忆,破碎支离—— 留连。人未归时,属水玄武,凡谋事二、八、十,走肾胃,贵人在南方,冲犯北方,小孩游路亡魂,大人乌面夫人。断曰:留连事难成,求谋日未明,凡事只宜缓,去者未回程。失物南方见,急讨方称心,更须防口舌,人口且太平。 就这样,外公凭他背得六十几万字的三国演义,识得易中的古之生荒,断得失物南方见的卦理,习得碑帖一般工整的柳体字,在合四山的古老围屋和几亩薄田上,活着。 凡题碑撰联,起课寻物,诵文祭悼一类,个杂前文中多有提及,不再详说。唯有一样,是外公去后这些年,我每每觉得生而维艰,偏又思及他时,所生的感悟—— 外公用来对付命运的,似乎只有一样武器,那就是他的快乐。 他坦受一切,绝不纠结。吃完酒席,你问他,他说,好啊,好啊;吃完焦糊的玉米碴,你问他,他说,好啊,好啊;穿件新衣裳,你问他,他说,好啊,好啊;披件褴褛褂子,你问他,他说,好啊,好啊;腿脚利索时,到处跑一身汗,你问他,他说,好啊,好啊;佝偻成鱼竿,一步一哎哟,你问他,他说,好啊,好啊。他就这么一直好啊好啊,好到眼斜耳聋,好到寸步难行,好到不闻惊雷,好到年近九十,坐在我家门口,依稀认出一个熟人,手搭凉棚问人家:“你爸爸他们还好唦?”“难为您家关心,我爸爸去年已经走了。”他确乎没有听见,似乎也没打算听见,笑眯眯地点头:“好啊,好啊。” 在他九十年的生命中,似乎只为一件事略做了些反抗。 谭家大宗族聚居的合四山,没有牌坊,不设祠堂,但“谭家”这两个字像极了烫金的烙印。仿佛从合四山出来的人,腾达是山的腾达,没落则是山的没落。他们无一例外,拼了命要出来,终于衣锦了,又拼了命要还乡。即便人生凋落,最大的遗愿也只是埋骨桑梓。 合四山几乎每家都有在外立了名望的人,所以大家难免一面相互庆贺,一面部分人以探亲之名,终于一去不回。不回的多了,气氛开始凋零,凋零本已习惯,却又岁月驹隙,竟有很多人次第辞世。总之,合四山的凋零之疾,终未痊愈。 外公作为谭家“一门三杰”的门长,自然是不能动的。在苹果园和紫竹林湮灭的时刻,他痛,在外婆身归那世的时刻,他痛,但这些痛,都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他守护者的责任感。六十岁以后,父母亲便劝过好几次,劝他不要再守了,搬下来和我们一起,也便于照顾,头摇得坚决,不允;七十岁以后,再屡屡苦劝,他只是笑,依然摇头,不允;八十岁以后,三个兄弟都走了,再劝,仍在犹豫,母亲急了,收了东西架起外公出门,算是绑架而归。终不是自愿投诚,得空便潜回合四山,在无人居住的老屋天井里久坐,笑眯眯地看石阶上的青苔,不寻不回。 今时,外公总算又回到合四山了,且再无人劝,他睡在那时的苹果园里,与外婆同在,与三外公相邻。想必夫妻时时说话,兄弟常能对坐,星光洒向草间的夜露,微风吹过熟悉的山岗,他一定会说—— 好啊,好啊。 4、根系 我自少时,便无可救药,学业稀烂,远嫌近烦,毫无合四山谭家枝脉之灵慧。 但对文字的喜爱,同样无可救药,除课本之外,愿饱读一切书籍,且能牢记二三。乡亲们说,你看,果然还是合四山藤上的瓜,根系上带的。 其实在我心里,合四山不过是湖北西部山区里一个寻常的山村,它唯一的不寻常,是那里住着我的外公。合四山是外公的合四山,与旁人无关。 并不乐意听见根系这样的词,仿佛我这个祖辈清贫的农家子弟,竟然还有一脉隐形的书香家风。我今日会的这些,皆由造化而至,不会的那些,也是机缘不巧,并没有什么东西在我的血管里奔涌,撺掇我不由自主地行文做人。 外公在我生命中的价值,在于他为我开了一扇门,使我寻到了一件可以玩一辈子的玩具。今天,我在北京的高楼里煞有介事地谋生,经常会与我的兄弟们闲话度日。他们说,可否帮我们列个书单?其实恕无告奉,现时里连朋友圈里那颇有来历的“好文推荐”,我都从未点开过,遑论标了外文作者姓名的“全球好书”呢?我悻悻地笑,想起外公逼我幼时所读的那些残卷:“增广贤文,朱子家训,围炉夜话,声律启蒙,菜根谭,夜航船。看完再找我。” 合四山总归是合四山,人去人来,楼起楼拆,树长树倒,花落花开。它是外公的全局,是我的场景,是轮回中无声的光斑和阴影。山里的故事被人读,也被人忘,走走歇歇,不过聚散一场。 一首小诗,山人同飨—— 书中草木风已碎,笔下烟尘月无亏; 苍天生我有吩咐,试为人间歌几回。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jinsiduna.com/jsdsb/9147.html
- 上一篇文章: 我撞破老公和白莲的好事,老公说她不是人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